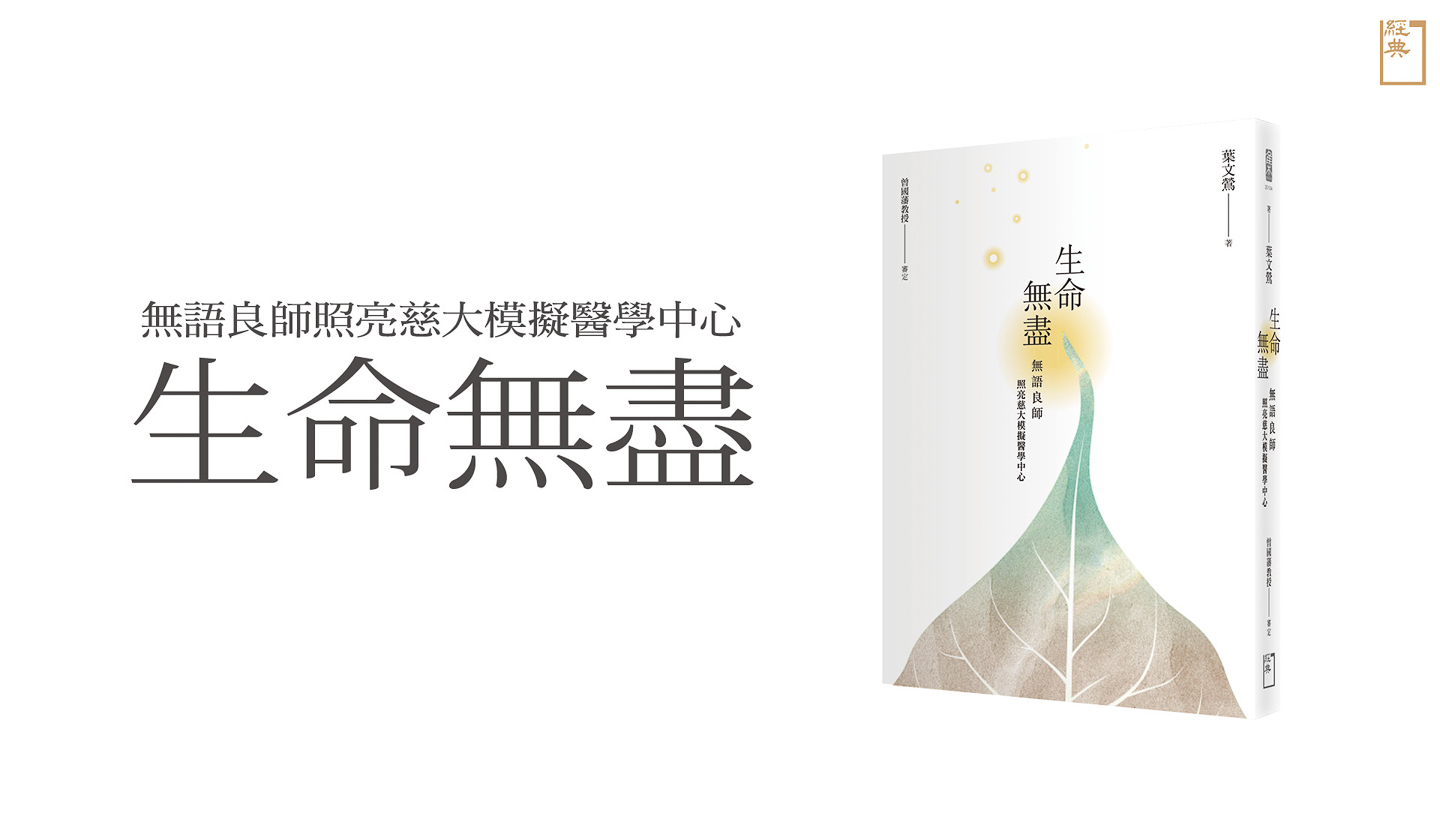「這些現狀如果讓死去的創辦人看到,我想他們寧可回到墳墓裡!」一名以色列集體農場的成員,比較過去與現在,忍不住痛下針砭。他繼續說:「我們延續了很多年集體生活的模式,就連內衣內褲都可以共享,大家樂於遵行共同生活的約定。但現在的集體農場竟然允許股市交易的市場機制進駐……我真的擔心,將來我們可能會淪為像義大利威尼斯的觀光船夫了。」身為以色列約兩百七十位集體農場的成員之一,他憂心指出:「也許未來我們要帶著象徵以色列國的傳統帽子,邊工作邊唱歌給觀光客聽。」
以色列「集體農場」的原文——「基布茲」(Kibbutz)——源於希伯來文「集體、共同」之意,由一群主張復國的「錫安主義」(Zionist)猶太知識分子實踐理想的行動,以軍事般的斯巴達教育為集體生活的準則。然而,眾志成城的烏托邦,仍不敵現代化與個人主義衝擊,逐漸瓦解成歷史中的榮耀記憶。
二十世紀初期,以色列的集體農場以一九一○年成立的「得家尼亞農場」(Degania)為首,開始在巴勒斯坦一帶成立。來自俄羅斯的猶太居民,十男二女,在鄂圖曼統治下的巴勒斯坦,選在約旦河岸開疆闢土。他們的夢想是要把東歐猶太社群的傳統意第緒語(Yiddish)徹底忘記,重新學習正統以色列的希伯來語。這群先驅者志不在農作,但一心一意想要改頭換面,成為「新造的人」,一如其他紛紛跟上的後來者,起而效尤,試圖以農耕方式來翻轉猶太世界。當時的巴勒斯坦周遭,土地貧瘠,到處是沙漠、沼澤與石頭山丘;加上公共衛生條件極差——瘧疾、傷寒與霍亂時有所聞——想要在如此情境下開設農場,需要投入大量資金。
凡物公用,平等至上
因為資源有限,無法各自耕田,加上安全考量,這群先驅者決定以集中生活的模式來建設集體農場。「猶太國家基金」(Jewish National Fund)集結了世界各地猶太社群的捐款,買地開墾。這群年輕人飽受披荊斬棘的艱辛,將荒蕪之地耕耘成農田,一如其中一名參與者所記錄的:「就算神勞形瘁、雙腿廢了、頭昏腦漲、烈陽曝晒而身心俱疲也在所不惜」。四年後,光是「得家尼亞農場」共有的麥田,已累積五十位成員並在巴勒斯坦茁壯,繁衍成數百個集體農場,最終甚至在新以色列建國後遍地開花。
這個自給自足的團體為勞苦耕耘的成員,提供一切生活所需。在七○年代前,集體農場奉行嚴格的公平原則,所有成員沒有屬於自己的東西,即便從他處獲取的個人禮物或收入,也一律要交出來。只有在五○至六○年代間,成員還能保有個人資產,譬如書籍與收音機,但車子則屬公共產物。
由於集體農場的成員沒有個人銀行帳戶,想要買任何東西都得經過委員會的核准。在這裡,凡物公用,同薪同酬,大家共同決定一切大小事。不論身分,每人輪流分工,一週下田,一週放牧,或到洗衣間工作。
集體農場顛覆了猶太傳統中的父權觀念,強調家庭與公平原則。這個烏托邦農場的創始元老,是一群不折不扣的性別平等擁護者,因此,男女都要下田農耕,粗活兒與防禦工作也都公平分配,但大部分女性還是得同時承擔婦女的傳統職責,包括清潔、縫紉、下廚等。在組織裡,相愛的男女可以要求一間屬於他們的房間,免除繁文縟節的婚禮,彼此認定了,便算是夫妻。這是另一個粉碎傳統父權宰治的行動,賦予女性自由選擇的機會,不必倚靠任何男人而活。一般家庭沒有廚房設施,吃飯時間到了,大夥兒便集合到公共餐廳共享餐點,因為集體農場的核心信念是,烹煮自己雙手耕作的食物,共享耕耘所得。為了訓練孩子們建立獨立生活的能力,這裡大部分的孩子住在「兒童之家」,父母每天只花兩小時陪伴小孩,其他時間則交由監督者照顧。這個「集體照養孩子」的教養模式,引起許多外人好奇,奧地利心理學家貝特罕(Bruno Bettelheim)甚至將集體農場對孩子身心發展的影響,寫成一本著名書籍《夢想之子》(Children of the Dream)。
對一些人來說,要遵守集體生活的共同規約是個挑戰,因此,數年後開始有不適應的新進成員紛紛退出組織。六○年代開始,集體農場的新生代女性成員竟一一回歸更傳統的性別角色,她們擁抱傳統婚姻,抗拒集體農場所主張的婚姻模式,捨棄祖父母所堅守的信念。
集體農場最初的概念,是以農畜產品的自給自足為目標,但理想與現實的落差,讓成員開始覺悟必須將觸角往外延伸,「世俗化」的經營模式顯然勢在必行。舉個例子,如果「得家尼亞農場」種蕉、養牛,那隔壁的「基尼烈農場」則專注發展宗教觀光產業,善用臨近的加利利海吸引朝聖的觀光客。
這個隸屬集體農場的「景點」,每年聚集了高達八十萬觀光客;來自全球的基督徒朝聖者絡繹不絕,只為親臨這條耶穌受洗之河。觀光客湧進購物中心,舉凡與基督宗教相關的物品,應有盡有,就連耶穌受難時被套在頭上的荊棘冠冕也買得到,還附有產品保證書。有些朝聖者會租借或購買白色的施洗繩索,帶著滿足的笑意浸入水中,體驗前所未有的施洗儀式,在聖歌的音效與感染下,經歷一種「重獲新生」的欣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