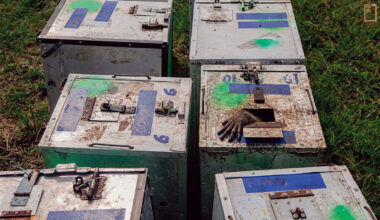我可以坐在牠們面前一整天,看牠們不知道在瞎忙什麼。牠們有一個小社會,有的護著卵、有的出去找食物,分工合作。」九月,演員孟耿如上傳了影片,興奮地向粉絲介紹家裡的新成員──螞蟻。
擁有十萬訂閱數、專門分享螞蟻飼養日常的YouTube頻道「臺灣蟻窟」,也在眾多貓狗頻道中異軍突起,光是一支幫螞蟻「加蓋樓中樓」(擴充蟻巢)的影片,就創造了八十八萬次觀看次數,讓不少人對螞蟻另眼相看。
台灣飼養昆蟲的風潮,最為人所知的就是二十多年前掀起的「甲蟲熱」。俗稱甲蟲的鞘翅目昆蟲,是昆蟲綱中最大的一目,也是動物界中種類最多的,像是鍬形蟲、兜蟲、金龜子、螢火蟲皆為鞘翅目。
一九九○年代後半,日本率先風靡甲蟲,沒多久台灣也跟上流行;二○○四年,隨著日本卡片遊戲機「甲蟲王者」的引進,更將台灣的飼養風氣推向最高峰,但也在五年內迅速退燒。如今趨於穩定,盛況或許不比從前,但甲蟲在愛好者的心中仍占有一席之地。
例如今年二十七歲的玩家孫紹鈞,養蟲資歷長達十五年,人生超過一半的時間都有甲蟲的存在。從小學校外教學時抓蟲回家,到現在育有巴拉望巨扁鍬形蟲、亞克提恩大兜蟲等五十多隻蟲,究竟飼養甲蟲的迷人之處是什麼?
「昆蟲不像貓、狗,牠們多半是出於本能反應,很難與人產生情感互動。我喜歡的是觀察牠們的生命週期,以及那種從蛋到成蟲、親手飼育的成就感!」孫紹鈞這麼說。
養蟲文化由來已久
事實上,昆蟲飼養的文化可以回推到一千多年前的中國。
台灣大學昆蟲學系名譽教授楊平世指出,最早源自唐代後宮女子養蟋蟀欣賞鳴聲,傳入民間後,興起鬥蟋蟀;而宋代有位「蟋蟀宰相」賈似道,著有世界上第一部蟋蟀研究專書《促織經》;明代出了「蟋蟀皇帝」明宣宗,讓全國上下捲入「蟋蟀風」。直至近代,台灣鄉間仍有鬥蟋蟀活動,人與蟋蟀形塑了民俗文化。
另外還有一種昆蟲創造了台灣人的集體回憶──上至六十歲世代、下至二十歲世代,只要是在台灣念小學,必定都有過「養蠶寶寶」的經驗。
「我還記得我會拿毛筆,輕輕地把蠶寶寶掃到新鮮桑葉上,非常寶貝呢!」三十四歲的昆蟲及生態講師呂軍逸笑著回憶。小學四年級的自然課,老師規定學生在家飼養蠶寶寶(家蠶),觀察牠從灰白細瘦變得白白胖胖,再到吐絲結繭、成為蠶蛹,羽化為蠶蛾後破繭而出的變態過程。
為了張羅蠶寶寶的食物,呂軍逸當時會與同學去文具店買桑葉或到路邊拔;即使呵護備至,他也遇過牠們拉肚子陣亡的慘況。只不過,等到蠶蛾順利產下大量的卵、孵化出黑壓壓的蟻蠶大軍時,這些蟲瞬間變成燙手山芋。「有同學說他不想養了,也有同學的媽媽拿去放生!」
橫跨這麼多世代的小學生都養過蠶寶寶,是因為台灣早年蠶繭及蠶絲外銷興盛,教科書商向蠶種製造場進貨蟲卵,再提供給老師作為教學。直到十年前,社會開始關注蠶寶寶的下場,教科書陸續改版,以觀察毛毛蟲(蝴蝶幼蟲)、竹節蟲或獨角仙為主;老師也傾向集體飼養在班上或自然教室,而非各自養在家裡,以免蠶寶寶悲劇重演。
成為講師後,呂軍逸曾詢問養過蠶寶寶的學生:「觀察到牠們有幾對複足?」但沒人仔細觀察過。像這樣「為養而養」,小學生從中獲得了什麼?
對人類的貢獻多多
「在台灣,種類最多的動物,不是鳥類、也不是魚類,而是我們身邊最常見、也最常被忽略的昆蟲。」楊平世指出。目前台灣已知的鳥類有六百多種、魚類兩千多種,昆蟲則高達兩萬多種,其中不少是本土特有種。台灣多變的氣候、多樣的植物相以及特殊地形,造就了能提供眾多昆蟲滋長與棲息的場所。
然而,不少人只從人類的角度將昆蟲分為益蟲或害蟲,甚至認為大部分是害蟲。在人類史上,確實有不少昆蟲造成災害,像是瘧蚊傳播瘧疾、家蠅攜帶霍亂病原、蝗蟲侵襲農作物造成饑荒,以及在台灣散播登革熱病毒的斑蚊、危害農作物的入侵紅火蟻及秋行軍蟲。但害蟲其實僅占少數,昆蟲不僅在自然生態扮演重要角色,更在藥學、醫學、科技等應用方面對人類有諸多貢獻。
生態系中,昆蟲既是多種動物的食物,也是顯花植物的授粉者,例如榕樹繁殖的關鍵就是榕果小蜂;並擔任自然界的「分解者」,例如可分解糞便及動物屍體的糞金龜。因此,在維繫食物鏈與食物網的穩定上,具有重要地位。
在藥學領域,中藥材運用昆蟲已久,《本草綱目》記載了十七目七十科以上的藥用昆蟲,如家蠶、蟬、蜚蠊(蟑螂)、胡蜂、蟋蟀、螞蟻。
而醫學方面,則不可不提果蠅的功勞。科學家以果蠅做實驗,不但證明了遺傳學的基因就在染色體上,就連幹細胞研究也得益於牠們,發現果蠅的細胞能由正常的組織分化到不同組織的超越分化。
在科技應用上,人類也向昆蟲「偷學」了不少靈感。例如,機器人手臂能全方位活動的原理,來自節肢動物之肌肉及神經系統控制關節的連接。又如太空科學中無人駕駛太空站或登陸於外星球自動展開的結構,就是參考金龜子後翅的摺疊及展開。
其他昆蟲的貢獻,還有評定環境品質時,會以出現的昆蟲種類與數量作為依據;偵查刑事案件時,也會藉由昆蟲在屍體上的活動與生長模式,推估死亡時間、地點或原因。凡此種種,對於這種「小動物」,人類真的不能等閒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