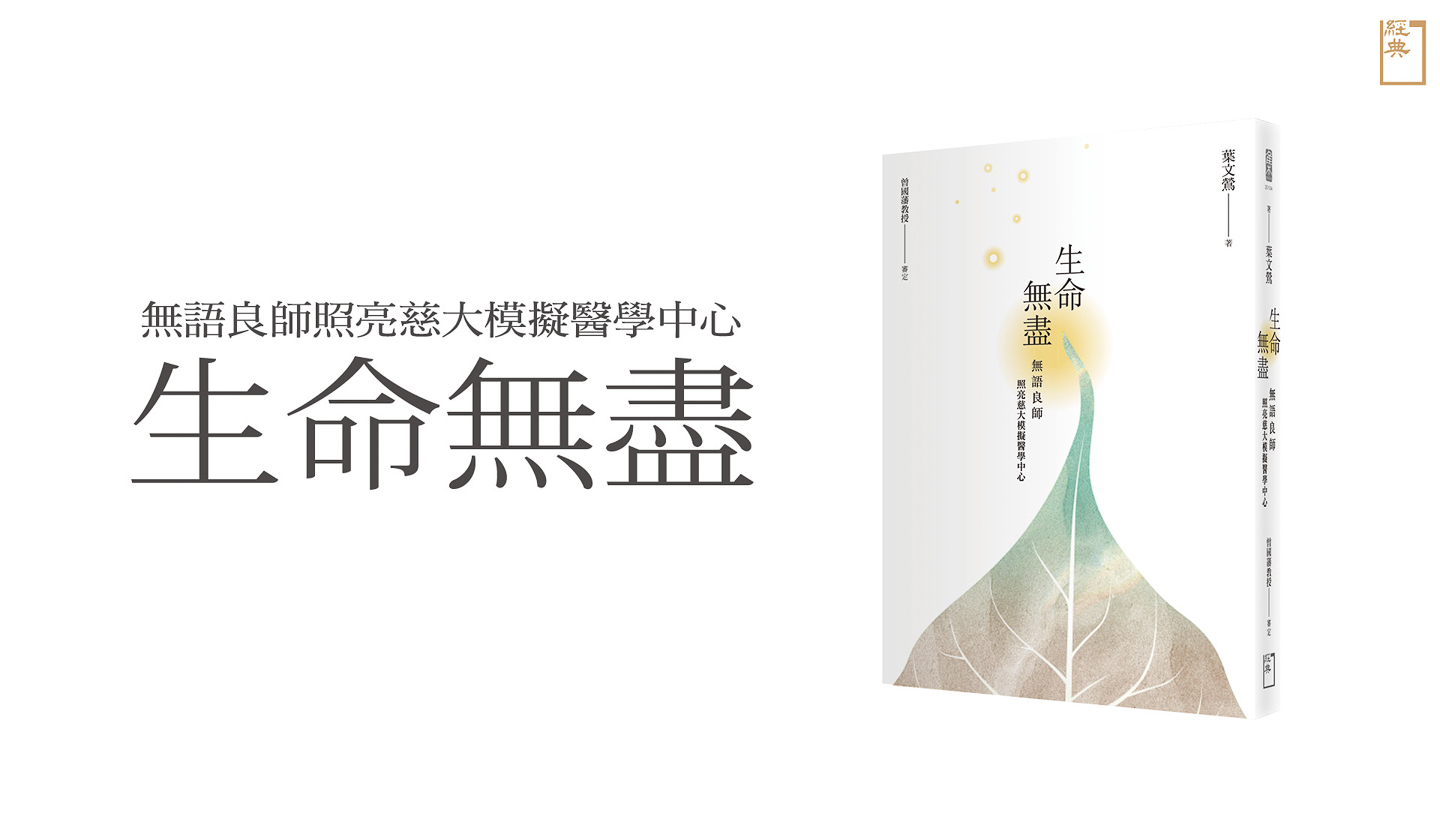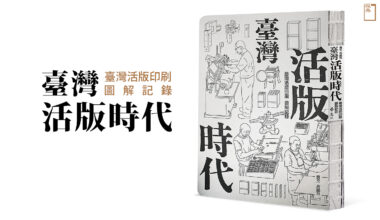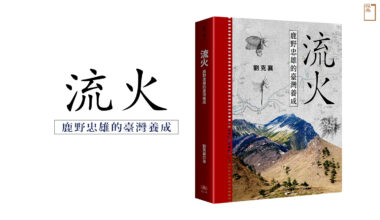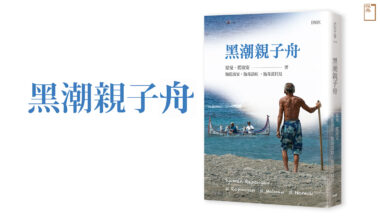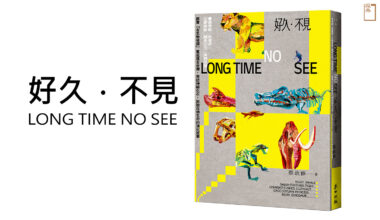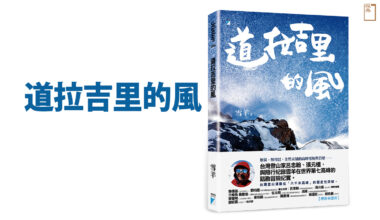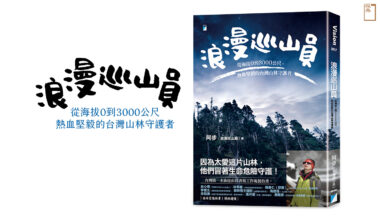良師與我
有一道光,比頂上的頭燈更加明亮,宛若天啟──「我們練習真的開刀!」的體驗,教張睿智深深著迷,他在那天立志成為一名外科醫師!
花蓮有著美麗的海洋,張睿智和同學買了釣魚頭燈──他們興致勃勃地──雖然不是用來登山溯溪、夜間釣魚使用,但他們需要一盞燈清楚照見一個很深、常人無法觸及的「黑洞」。
他們知道那裡面有什麼,卻不曾用這種方式進去探險。這頭燈的角度可以旋轉,還能分段變焦,足夠派上用場了!他們很開心這個價錢學生買得起。
慈濟大學解剖學科曾國藩、王曰然老師花了一年多的時間開發「大體模擬手術」,最特別的是「無語良師」以急速冷凍方式保存,回溫之後,將由花蓮慈濟醫院外科醫師指導他們這一屆畢業生如何「開刀」。
作為醫療用品之一,這頭燈的等級似乎應更高級一些,由於價錢、用途明顯落差,突兀地讓人覺得好笑!可令他們真正好奇的,是這一堂國內首創使用全人冷凍教學遺體的「模擬手術」課。
實驗教學的地點在大三的解剖實習教室,張睿智想像躺在解剖臺上的無語良師,和四年前在大三解剖實習課完全不同;冷凍回溫的身體應和真人一樣柔軟,當手術刀畫開大體老師柔軟的腹腔,裡面的臟器和腸子應該都會流動吧?相當「逼真」的「模擬」,幸好曾國藩老師說,冷凍保存的大體老師不會有血流。在經驗不曾到達的地方,人們帶著好奇、興奮和期待。慈大醫學系第二屆張睿智這一班,在大七畢業前夕面對另一批「無語良師」,將手上的解剖刀換成手術刀。
雖然醫學生還無法治療病人,但能透過手術模擬而進入臨床實習的狀態。來不及爬梳心中的五味雜陳,他和同學們帶著虔誠之心,打開一具具神聖的人體。沿著事先做好的標記線,張睿智輕輕畫開大體老師,隔著橡膠手套,滲著水珠的血肉之軀令人感到冰冷。在外科醫師的引導下,他們指認了一些臟器。僅隔一層皮肉,裡面就是另一天地!雖然無語良師並沒有闌尾炎,他們仍藉以模擬外科最簡單的肓腸手術,之後又練習如何接通腸子和簡單的縫合等。
從基礎醫學跨進臨床醫學的門檻,在入門的那一刻,張睿智的眼睛發光!這道光宛若天啟,比頂上的頭燈更加明亮,讓他照見未來的方向,確立要當一名外科醫師!
史無前例的大體捐贈因緣
張睿智從醫學院畢業的十六年後,二○一八年八月二十四日,曾國藩、張睿智師生聯袂出席經典雜誌創刊二十週年慶系列講座,在台北松山文創園區以「零下三十度的愛」為題,針對「無語良師」、「模擬手術」議題展開對話。
這年七月,張睿智甫升任花蓮慈濟醫院外科部主任,是慈濟體系培養出來的心臟外科醫師,師長們眼中的驕傲;而伴隨一路成長、在他感恩的對象中唯獨無法出席的,是成就他學醫路上最無私奉獻的——「無語良師」們。
往者無法親臨,但,有家屬來了!其中,坐在臺下的康蕾阿姨,是張睿智大三解剖學課無語良師康純安爺爺的次女。她在一對子女的陪伴下遠從高雄北上,專程來聽「小睿」演講。
康蕾與張睿智的媽媽和小提琴恩師等親友同坐一起,用她發亮的眸子看著臺上的大男孩。自從在康爺爺的大體啟用那天初次見面,二十一年來,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繫,同年六月也剛在慈濟大學見過。
那是個悲欣交集的日子,康家大姊念慈的大體在模擬手術啟用,她是這個天主教家庭的第二代捐贈者,父女倆的大體捐贈間隔了二十二年,同樣將身體奉獻給慈濟大學。張睿智以家屬身分,參與了康大阿姨的大事,從大體啟用直到送靈典禮。在大體啟用前一天的行誼介紹,張睿智、蘇桂英夫婦與康阿姨的家人坐在一起。康蕾一見到小睿下班後趕來,先是摸摸他的頭,接著牽起他的手撫挲著。她既感動也感慨,心疼他臉上帶著倦容,在這樣的夜晚與他們同在。
康念慈捐作模擬手術的決定,與張睿智直接相關。回溯在他的畢業典禮,當時,康家姊妹前來祝賀張睿智這一組四位醫學生即將踏上嶄新的里程。
「康阿姨,我們練習真的開刀!」康蕾注意到小睿說話時眼睛發光。
「原來慈濟大學也有模擬手術啊!」康念慈當時就說將來也要「捐這一種」,康蕾也是。
一九九六年,康純安爺爺往生捐贈大體時,慈濟還沒有發展出模擬手術。基於臺灣的醫學院缺乏大體,難以培養出好醫師,康爺爺捐大體的心願也直接影響子女,康家姊妹認為模擬手術可能更接近爸爸的理想,可讓醫學生在進入臨床實習前先充實基本的技術。
於是,二○一八年元月,七十歲往生的康大姊來了!她追隨父親的步履、奉獻醫學;隨著慈濟大學在大體教學水準的升級,康念慈所捐贈的身體,亦將面對不同以往的教學體驗。
捐贈者家屬的出席、兩代之間的大體捐贈、捐贈者家眷與醫學生持續二十年以上的情誼,宛如一家人……,凡此,皆是慈濟「無語良師」特殊的醫學人文內涵,放眼中外、史無前例!
絕無僅有的溫馨互動
昔日的大三醫學生,如今是一名優秀的外科醫師,張睿智與當年同組學習解剖的蘇桂英,畢業後雙雙進入花蓮慈濟醫院服務並結為伴侶,之後同赴美國杜克大學深造,兩人分別取得實驗病理學、免疫學博士。蘇桂英目前服務於花蓮慈濟醫院風濕免疫科。
他們在學期間,蘇桂英放暑假會去找康阿姨。張睿智在慈院服務從美國進修回來,遇南部出差的機會,也特地停留高雄見見康阿姨們。而今,他們的孩子喊康阿姨叫「姨婆」呢!
曾國藩教授肯定這樣的互動關係是真正進入醫學生的心,而不只是應付校方要求而已。
在「零下三十度的愛」這場演講,張睿智帶來一個始終小心翼翼保管的紙袋,裡面珍藏二十多年來康阿姨們送給他的禮物,有莫內畫冊、美金紅包—用意不在幣值多少,而是鈔票上面的數字編碼與張睿智的生日數字相關;知道他從小就學小提琴,康阿姨也送了一個精緻的小提琴造型工藝品。都是平日用心蒐集的小物,無論在他生日、畢業或結婚等,康阿姨們都歡喜祝賀。張睿智指著紙袋裡康阿姨寄來的剪報,標題是「康復你的心靈」。他笑說:「康阿姨大概知道我內心比較脆弱!」
他確實差點在解剖實習課卡在康爺爺的胸膛過不去。那是大體啟用後兩、三週,實習進度必須使用電鋸取出無語良師的胸骨。
「那是康爺爺啊,太殘忍了!」張睿智週末回到家,一進門抱著媽媽哭了,他認為沒辦法繼續念下去。
媽媽鼓勵他不要辜負康爺爺捐贈的心意。之後他在學校做了一個夢,夢中出現一位白衣老人對他說:「不要怕,來吧!」康阿姨說,夢中的白衣老人應是康爺爺,請小睿儘管在她爸爸的身上學習。
康家子女每隔兩、三週就到花蓮,「一個學期來了八次。」張睿智記得康阿姨從高雄帶點心去慰勞他們,對於他們解剖的每一個發現都深感興趣。
「我們了解爸爸的思想行為和對我們的愛,他追求健康,可是他身體裡面的情形我們不知道。」康蕾似乎遺傳了爸爸的好學求知精神。
康爺爺一向飲食有節、起居有常,每日晨起練功,家族也有長壽基因,卻在七十九歲時罹患直腸癌。康家祖父是中醫師,耳濡目染下,他沒有選擇開刀而採中醫緩治,子女多方蒐集資訊,包括身體排毒、腳底按摩,也服用天然藥材,希望可與疾病和平共處。癌症本不宜進補,但為了讓日漸消瘦的身體強壯一些,不意導致病程一發不可收拾,子女依其遺願,成全他捐贈大體。
「康爺爺的肝好大,心臟也好大喔!」「康爺爺的血管很乾淨!」聽著張睿智、邱彥程、蘇桂英和陳美淇這一組醫學生說起在康爺爺身上的觀察與發現,康家姊弟興味十足,絲毫沒有一般人以為的人體解剖是多麼殘忍的事!而這樣的陪伴也讓醫學生安心,並充實地修習這門艱深的醫學入門課。
康蕾認為培育醫學生將來行醫救人,這是善事,古德有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她記得爸爸生前觀看電視「Discovery」頻道,介紹國外一位身高一百八十公分的死刑犯,執刑後身體被以一公分、一公分切片做成人體解剖教學動畫。當時爸爸看得目不轉睛,告訴康蕾希望自己也被做成這樣的標本。
「爸,您這麼老了,骨頭也酥了,人家不會用你的!那個人年輕,身體是標準的!」康蕾幾乎笑著說。
「可以有年輕的,也有老的,學生才有比較。」
「台灣人不可能這麼做!」康蕾想打消爸爸的念頭。
手術靠勤練,非華麗演出
張睿智大五開始到醫院實習,發現自己很喜歡照顧病人,不同於念書考試,在醫院遇見病人的狀況,「不會就是不會,一翻兩瞪眼。」他體會必須趕緊學到救人的技術。
在學會真本事之前,同學之間僅能比較值班時候的「運氣」。張睿智似乎遇到較多的考驗,病人若不是必須急救,可能就是咳血、吐血、呼吸喘……,不會處理就幫不了忙,這也激發他開始認真學習,從大五到大七,他希望能對病人負責。
在外科學習,他經常把開刀房手術後用剩下的縫線,挑些乾淨的帶回家,有時縫合處在身體內部極深、無法直視,所以他練習在黑暗中綁線—這是外科醫師最基本的功夫—直到熟練為止。
他說,心臟是立體的,無論切除或是縫合都比較困難,開刀尤其和手指活動的精細度有關。有人以為開刀就像電影裡面,演員的動作好像很華麗、很帥氣,其實不然。
「只要平日勤練,每個基本動作做好就會很扎實。」張睿智認為手術是最樸實的訓練。
跟隨心臟外科趙盛豐、張比嵩兩位師長學習,無論是傳統的心臟手術,或是近幾年不斷發展的微創手術,雖然僅在病人身上打開幾個小傷口,但在身體裡面操作器械卻是大動乾坤。
藝高不敢膽大,過程不敢掉以輕心。張睿智更分析,慈濟醫院的心臟外科手術在二○○六、二○○七年到達頂峰,之後隨著心導管技術的進步,很多病人在內科就能獲得處理,因此每年病例下降至一百到一百二十例;但這也表示只要轉至心臟外科的病人,難度就變得更加複雜。
微創手術不需要鋸開胸骨,病人傷口小、術後復原快,這是心臟外科手術的趨勢,張睿智得空習慣靜下來思考如何做心臟微創手術,接著與團隊利用慈濟大學模擬醫學中心練習,譬如這些年做過微創心臟瓣膜置換與修復手術、主動脈瓣膜置換術、冠狀動脈繞道手術等。
心臟手術的時間約四到六小時,雖然模擬手術並未「真實」到使用體外循環機,卻可藉以熟悉人體臨床解剖,清楚掌握手術步驟;指導老師也會適時提醒成員手術注意事項。張睿智在無語良師身上練刀,一直到現在,他強調外科訓練無法僅靠知識或影像教學。
他記得在慈院心臟外科住院醫師期間,雖然有資深醫師,但是很少人在做微創心臟手術,「任何一件事不一定要有『人』教,運用各項資訊,從文字、圖片和影像到觀摩,」張睿智指出,到了這裡算是「無師」仍可學習,接下來若要能「自通」,「只要在無語良師身上做過,我就有信心在病人身上做是安全的。」他肯定模擬手術對自己有著莫大的幫助。
康念慈老師──
一張照片,天涯海角、世世代代
在三月,康念慈笑燦如花,如瀑的長髮自肩頭垂下,恰似她亮麗而溫柔的個性。如今,只剩下一張照片了!
「我們家都叫我姊姊『阿大』。生前她進出醫院數次,我不知道為什麼,覺得只要姊姊進了醫院後,都能跟著我回家;但這次是天主的安排,帶姊姊去了更好的地方,雖然我們都很捨不得。我們都愛你。」二○一八年三月,小妹康嘉梅在大姊的追思彌撒代表家屬致辭。
一會兒對著眾人說話,一會兒又捨不得大姊,致辭結束臨下臺,她轉身摸摸照片上姊姊的臉頰,說:「阿大,我還是喜歡活著的你。」
那是康念慈去世的兩個月後,她的大體已經存放在慈濟大學,準備在六月的模擬手術課程啟用。七十歲的她追隨爸爸康純安的腳步,相隔二十二年,爸爸當年八十歲逝世,兩人身後都將大體捐贈給慈濟大學。
「奉獻醫學、不與活人爭地,只要留張照片加上一則生平事蹟就可以了。」孝順的康念慈一向聽從爸爸的話。
上帝與佛陀的雙重祝福
來自高雄天主教家庭的這對父女,相繼捐贈大體給佛教團體創辦的醫學院。
爸爸在一九九六年捐贈時,慈濟醫學院剛創校兩年多。他的第一志願是將大體獻給全台最優秀的醫學生,或捐給就近的醫學院。雖然爸爸保留一分證嚴法師呼籲大體捐贈的剪報,但花蓮交通不便、距離太遠,不在優先考慮之列。
爸爸形容癌細胞是一家「無限股份公司」,自知不敵,便一再催促女兒早日為他安排好捐贈事宜,康家姊妹遲遲不願進行。她們知道一旦爸爸心無掛礙,應該很快就會離去。
直到他病重,女兒才開始聯繫各家醫學院,過程中被告知若是農曆過年期間往生,因學校無人值班,請家屬先自行送至殯儀館;也有人員聽說是子女主動打聽遺體捐贈,還責怪他們不孝。
在茫然無措時,康家姊妹想到任職於花蓮慈濟醫院胸腔內科的老朋友楊治國醫師,透過他聯繫了慈濟醫學院。遺體處理人員陳鴻彬、張子湘隨即偕同高雄慈濟委員湯吉美到家中關懷,詳細告知後續處理事項,並在爸爸去世前還來探視他。「慈濟在人文禮儀方面做得最周到。」康念慈那時便肯定慈濟對於大體志願捐贈者與家屬的尊重。
二○一八年元月,康念慈的大體捐贈同樣由陳鴻彬、湯吉美和楊治國醫師原班人馬關懷陪伴。
康念慈是在二○○二年參加父親那一組醫學生的畢業典禮,從「小睿」張睿智口中得知慈濟大學醫學系開發了模擬手術,當時便決定日後將捐作冷凍保存的大體,讓醫學生練習開刀,直接應用在臨床。
花蓮慈院心臟外科張睿智醫師記得,二○一七年十二月,太太蘇桂英才和康大阿姨通過電話。
「大阿姨什麼時候再到花蓮啊?」蘇桂英問。「有計畫,應該不久就會去。」康念慈沒有告知病情,不想讓他們夫婦擔心。就在元月,康念慈病逝於台北。康嘉梅陪著大姊搭乘救護車前往花蓮路上一路暈車。以前稍有不適,學過氣功的大姊都會幫她調理,曾有朋友形容她對大姊重度依賴的程度簡直到了「若你大姊不在了,你就『死』了!」
雖然自大姊癌症復發病重以來,她開始學習獨立,但她無法想像一日沒有大姊,她該怎麼辦呢?果然第一天便如此難熬。
一路的曲折終於抵達慈濟大學,其他家人猶開車尾隨在半途。那天正巧是慈大一個梯次模擬手術課程結束,無語良師送靈典禮的午後,家屬們剛從火葬場領回骨灰。僅剩十五分鐘就要開始入龕典禮,靜思精舍的法師們特地迎接與慈濟因緣深厚的無語良師康純安老先生的女兒康念慈。
「師父讚美姊姊好莊嚴,為姊姊念佛十五分鐘,他們都沒休息接著就主持入龕典禮。」康嘉梅永遠記得那一刻鐘。
「太殊勝了!這是天主安排的十五分鐘!」陳鴻彬當時也這麼說。
歸回天家,寧靜的騷動
大姊歸回天家時,嘉梅認為應讓大姊的朋友知道,於是以大姊的手機通訊錄傳送消息。
怎麼會有人使用自己的手機發出自己的死訊呢?「一月十九日並不是愚人節,康老師不可能開這種玩笑!」接到訊息的人不斷打電話來求證,陣陣鈴響都讓小妹不得不忍住悲傷,告知原委。
接連地,各地的教友為大姊舉辦告別彌撒,積極的人還組成治喪委員會。
「姊姊右手做的事都沒讓左手知道。」嘉梅說,她這才明白大姊過去每日每夜,或說是沒日沒夜地在外都做了什麼,難怪有那麼多人敬愛大姊!
「大姊自知時間有限,所以一直做……。」她不禁黯然。「阿大,你回來了怎麼不上床睡呢?」想起昔日夜半起身,經常看見大姊坐在客廳地毯上,上半身斜靠在沙發休息。也許是從外面回來累了,有時只是暫時歇會兒便又漱洗更衣出門,總是席不暇暖。
「大姊不設鬧鐘,而是依生理時鐘,我們早上起床,她已經出門了!」二妹說,爸爸在世時,事親至孝的大姊最晚半夜一點鐘就會進門,為了不讓他老人家擔心;爸爸走後,大姊到家的時間就更晚了!
「睡眠,是窮人最好的補藥。」大姊沒有聽進爸爸的這句叮嚀,體力長期透支。「她不是有體力,而是靠意志力。」小妹說,大姊充滿愛的能量,才能在外奔波不疲累;即使生命最後在北部住院,依然每天四點多起床,五點準時用手機傳送六百多通福音給教友。
「她的生活都是信仰,都是愛人!」如妹妹們所說,大姊一向主動關心別人。她在中正預校任教期間,連年榮獲模範教師的表揚。在每學期開學前,她都會整理學生資料,熟知學生的家庭背景;每週二晚間,她利用學校圖書館義務為學生提供心理輔導,幫助他們了解性向,猶如慈母般引導學生在未來的職涯不致迷茫。此外,若在課堂上發現學生學習不夠專心或是神情有異,也會找時間私下詢問。一位單親家庭的學生,愁著從事清潔工作的媽媽無力支付全口假牙的費用,康念慈得知後,不但提供安裝假牙的費用,還額外給學生一筆錢讓媽媽購置營養品。無意間發現一名學生脖子上有腫塊,她直覺事態不妙,當週即陪同學生返回中部的家,建議家長不可輕忽。經檢查,學生不幸被確診為淋巴癌,在休養期間,康念慈常利用假日往返探望。
「在我們家遊必有方,大姊都會事先跟爸爸講。所謂的孝、悌、忠、信,她都做到了!」嘉梅在大姊走後,環顧爸爸親手建造的這棟樓房,這個家先是走了呵護她的媽媽、爸爸,再來是大姊,重大的失落讓她這個家中小女兒暗自哭泣了將近五個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