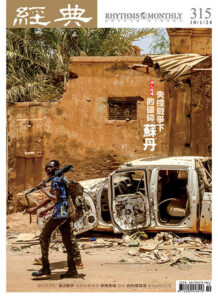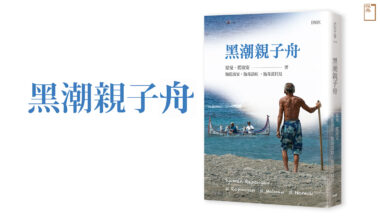風雪、星子、道拉吉里
——不要告別!
世界第七高峰道拉吉里(Dhaulagiri)的名字來自梵語,Dhaula意指「耀眼、潔白、美麗」,Giri則是「山」的通稱,海拔高度八千一百六十七公尺,隔著一道卡利甘達基峽谷(Kali Gandaki Gorge)與世界第十高峰安娜普納(Annapurna)遙相對望。
世界超過八千公尺的巨峰共十四座,其中八座位於尼泊爾境內,而道拉吉里是最西邊的一座,沿著喜馬拉雅山脈往西北,再無更高的山峰,一直要到巴基斯坦境內的南迦帕爾巴特(Nanga Parbat,海拔八千一百二十六公尺,當地烏爾都語是「赤裸之山」之義),才戲劇性地為地表最大造山運動收束了一個結尾。
在八十年前的世界八千米巨峰挑戰賽中,安娜普納是最先被人類足跡踏上的一座,南迦帕爾巴特是最先被歐洲人嘗試攀登的一座。話雖如此,兩座大山奪走人命的數字和成功登頂者的比值都相當高,相較之下,道拉吉里看似親切許多,但也絕不是一座容易的山。因為地理位置靠近印度邊境,沒有其他山峰的阻擋,英國測量隊早在一八○八年就發現它的山巔,咸認道拉吉里就是世界第一高峰,直到分別三十年與五十年後,大三角測量隊接次發現了干城章嘉與聖母峰為止。
道拉吉里的人類首登紀錄發生在一九六○年,一支由瑞士、奧地利和雪巴人組成的遠征軍,成功地由東北脊攀上峰頂。它是十四座裡倒數第二個才被攻克的巨峰,部分原因是探勘可行路線花去不少時間,它直面印度平原的南壁,既垂直又高拔,峰頂下有一道三百米高的花崗岩環帶,是難關中的難關,至今仍無人能經此路線達陣,號稱為「喜馬拉雅最後障礙」。爾後的攀登者絕大多數都走初登者開發出來的東北脊,在天氣狀況好的情況下,成功登頂的機率非常高。
為什麼要去攀登道拉吉里山呢?台灣兩位登山家呂忠翰(人稱「阿果」),是已經許下志願要成為無氧攀登十四座八千米巨峰的攀登者,尚未完攀的道拉吉里是他的必要功課之一;張元植在經歷二○一九年世界第二高峰K2的未竟之役後,決定選擇走跟阿果不一樣的道路,著重於冰雪岩混合、美感路線的技術攀登。
此次兩人決定不走傳統路,瞄準著尚無人成功走過的西北稜脊,是覺得如果能攻破兩個難關的煙囪地形,上到雪原後,即使沒有成功登頂,那也看到了世界無人看過的風景,便值回票價。作者雪羊既想要成為兩位大哥的冒險行動紀錄者,也想嘗試走傳統東北脊路線,或可寫下生命中第一座八千大山的紀錄。
故事的結局與三個人的期待不一樣,所有的目標都沒有達到,然則,這也是高海拔紀錄吸引人的地方——在都市中的文明人,來到大自然的不毛之地,不論是知性或感性上,都會蛻上好幾層皮,而這一段切身而不免疼痛的歷程,是無法在生命的安全帶之內感受到的。《道拉吉里的風》一書所描寫的,正是各種困難交織下,三個台灣年輕人如何跟來自大自然與異文明,甚且自身內在心魔的搏戰,所留下的真摯紀錄。
(推薦序/詹偉雄)
2023年5月20日,下午4:50
通往道拉吉里第三營的冰坡
尼泊爾,道拉吉里峰,海拔7,240公尺
在空無一人,堅硬到每一步都需要將冰爪稍微使力才能踢進冰面的陡坡上,我沿著緊繃的白絞繩,左手推著上升器,右手緊握冰斧,獨自緩緩前進。這時的我,呼吸急促地像氣喘發作般緊湊,紊亂的行走節奏也讓我每走一步都需要休息一兩秒才能跨出下一腳。
從海拔六千四百公尺的第二營出發後,已過了將近十小時,累積的疲憊與第一次突破海拔七千公尺的不適應,侵蝕著我的身體,也讓我成為這批攀登者中最後一個抵達第三營的人。
阿果來過這個營地,知道那是簡陋且不舒服的地方,因此一早出發後就全速前進不見蹤影,只為了幫我們挑一頂最好的帳篷,並整理舒服。七千公尺的環境,嚴苛到強壯的雪巴人已無法提供自己帶的客戶專屬帳篷,只能和同公司的其他隊員共用營帳,還得先搶先贏,晚到就只能睡奇怪的地方。元植速度沒有阿果快,而曾登頂梅樂峰的我,在超過六千四百七十六公尺後,每一步都是人生新高,他便所幸陪我一起前進,一面教我高峰攀登的步伐節奏與技巧。
接近中午左右,元植看我走得不錯,就留我一人慢慢努力;畢竟等人是很累的事,每個人各自用自己舒服的速度行走,才是高峰攀登的常態。而拉卡帕從抵達道拉吉里基地營以來,身體就一直不舒服,因此我早早請他照著自己的節奏走,背負氧氣瓶趕快到第三營休息就好,我可以獨自背負所有的個人裝備。
然而,我低估了七千公尺的威力。就算已在海拔四千六百公尺以上的道拉吉里基地營待了一個月,也做過兩次完整高度適應,還在海拔六千四百公尺的第二營睡了兩個晚上,但「七千公尺」這個海拔級距,對我而言終究是一個全新的極端環境,妄想第一次就有好的表現實在太勉強了。
突破海拔六千八百公尺後,我便發現自己漸漸找不到呼吸與步伐的節奏,時常沒幾步就得停下來大口喘息,好像被抓離水面的魚,拚命張嘴,卻只能吸進一片虛空。那種無論再怎麼吸氣,總是覺得不夠、肺泡永遠填不滿的感覺,會讓一切都慢下來。因為肌肉只要動得快一點,氧氣的補充便會趕不上消耗,所以高峰攀登的體能表現,都會隨著高度打折再打折。
高度突破海拔七千一百三十四公尺後不久,路邊剛好有幾捆雪巴們棄置的白絞繩,於是我拿它們當坐墊,將冰斧插進冰面、鉤環扣上固定繩,然後解開上升器、卸下沉重的背包,放任時間流逝,肆無忌憚地大休了起來。
「七一三四」這個標高,正是二○一八年讓我鎩羽而歸的吉爾吉斯「列寧峰」的海拔高度。那年的緊張、痛苦、懊悔、遺憾,全都在這一刻湧上心頭。然而,舉目所及只是冰雪的藍白與凜冽的氣流,那曾經的失敗成為了此刻的養分;在這裡休息,象徵著我突破了當年未竟的夢,繼續往高處走去。
風不斷吹過潔白透亮的冰面,掃起一陣陣的雪沙,噴得連身羽絨沙沙作響,也刺痛著我的臉頰,雲霧也慢慢聚攏過來。該走了。望向剛剛超我車的俄羅斯隊,又多往上爬了五十公尺,我小心翼翼地將上升器重新掛回固定繩上,撥掉身上的雪粒,拿出保溫瓶喝下珍貴的溫水,準備面對現實,用約莫每小時爬升六十公尺高的速度做最後「衝刺」。
這個速度,只有我平常在台灣爬山的六分之一,甚至不到。
下午四點五十三分,我終於看見除了冰、石頭、雪與天空之外的人造物了。出現在視野裡的鮮黃帳篷與周圍四散的垃圾,是第三營鐵一般的存在證明,心中一陣狂喜:「終於到啦!慢俄羅斯隊三十公尺而已,不算落隊!」雖然在俄羅斯隊的身影旁,有一頂上下顛倒的帳篷,正隨風不斷啪嗒啪嗒地飄蕩、撞擊著地面,且舉目所及根本沒有什麼平坦腹地,讓我擔憂起第三營的休息環境。
又前進幾步,離帳篷區更近了些,我忍不住大聲歡呼。然而下一秒煩惱便浮上心頭:已經快五點了,表定是今晚八點準時出發衝頂,就剩沒多少時間休息了,我們的帳篷究竟在哪呀?
「羊羊!你到了,趕快進來!」這時,營地最下方的帳篷裡竟傳來元植的聲音。原來這就是阿果中午前抵達第三營,巡完整個營地後決定的落腳之處。
元植拉開前庭和我四目相對,這伸手可及的安心,讓我瞬間放鬆下來。我解開背包,擠乾剩下的力氣將它輕輕交給元植,裡面有兩台摔不得的寶貝相機,然後才像是終於放下戰利品的工蟻,長舒了一口氣。
「這也太重了吧?!你這樣根本是重裝上列寧峰啊!」擅長輕量化的元植挺出半截身子,接過緊繃氣球般的背包驚呼著,彷彿捧著一隻即將生產的孔雀魚。「大概有十五公斤吧!難怪你走成這樣,很不錯了啦,快進來!」他像隻活板門蛛,迅速連人帶包縮回帳篷裡。我順勢踩進前庭的空位,小心翼翼地轉身、彎腰,讓屁股先進帳篷,上半身再一口氣探入,用一種跌坐的方式跌進帳內,直接躺在元植大腿上,穿著冰爪與雙重靴的腳還留在前庭。
這頂小小的三人帳,擠進了穿著連身羽絨衣的元植、阿果和拉卡帕三人,原本就是肩並肩動彈不得的狀態,此刻我就像一杯水,倒入裝滿砂石的水桶中,填滿最後一絲縫隙。嚴格來說,是讓原本二維排列的三人,調整成三維交織的狀態:我躺在元植身上,元植躺在阿果身上,拉卡帕躺在阿果腿上,而他正坐著等我把腳收進來。
攀登八千米的過程中,約莫超過海拔七千公尺後,便需要開始穿著特製的「連身羽絨衣」。這是一種從頭包到腳的特殊一體式套裝,在最高溫不到零下十度的環境中,為高峰攀登者提供溫暖與保護,是八千米等極地攀登專用,用途極度侷限卻又不能沒有的裝備。
無論爬哪座八千米,人們通常會在海拔六千公尺左右的第二營穿上這件衣服,直到登頂後回到六千公尺區域才會脫掉。而這件衣服的缺點除了很貴,就是穿上後體積會增為兩倍,和「米其林寶寶」一模一樣。當代的八千米攀登,就是幾十、幾百隻五顏六色的米其林寶寶,奮力地在風花費萬年雕琢出的冰雪雕塑上掙扎前進,追尋自己的價值。
「恭喜羊羊,順利到達三營!又突破自己啦,兄弟!」阿果開朗的嗓音迴盪在帳篷裡,我回頭看向他,擠出一抹笑容。他馬上和元植說:「哇,我們的羊羊累到鏘掉了,那個眼神都快不能對焦了。」「把你的氧氣面罩和調節器拿出來。」「拉卡帕,給我氧氣(瓶)!」
與其說登山者很真誠,倒不如說人的體能一旦瀕臨極限,連戴面具、演戲的能量都不剩了。這時唯一拿得出來與人相處的,就只剩下本性。因此,在攀登八千米時,有一個判斷攀登者還有沒有餘裕的最佳指標:能不能照顧自己。
除了眼神外,他們倆並不覺得我狀況不好,而事實也是如此:我感覺到自己很接近極限,但還沒到,我還想多做一點事。肆無忌憚地在元植身上伸展一陣子,用要把帳篷抽真空般的深度,貪婪大吸好幾口氣後,我總算回復一些體能,直起上半身,開始脫鞋。
除了連身羽絨衣外,高峰攀登最重要的裝備之二,就是鞋子。在海拔六千公尺以上的冰封地帶中,唯有特殊設計的「雙重靴」能提供足部溫暖與保護。然而,這種鞋子體積很大、重量非常重,且通常做得很合腳,因此自從這個裝備誕生以來,「脫鞋」這件事對攀登者來說都是一件很累人又麻煩的事。在許多高峰故事裡,常看見攀登者穿著鞋子睡覺,又或者雪巴人幫客人脫鞋子的場面,大多是因體力耗盡所致。想像一下,在一個講話快一點就會喘的環境裡,要弓身使勁脫掉腳上光一隻就重達一點三公斤的大鞋,會是多耗費力氣、多需要耐心的事?
過了十分鐘,我總算把鞋子脫下來。七千公尺的空氣實在太稀薄,我光脫完一隻腳,就要先停下來大喘幾口氣。阿果那邊也沒閒著,把我的氧氣面罩和調節器裝上氧氣鋼瓶,看我終於搞定一切,就把面罩遞過來。「把面罩戴上,吸氧很快就恢復了。」
我心裡有點抗拒,想把氧氣留到登頂時再吸,多爭取幾步有氧氣的路途是幾步,但也僅止於「想」。當下十分疲憊,甚至開始微微頭痛的我,還是乖乖把手伸了過去。
「嘶——」戴上面罩後,阿果把開關打開,新鮮氧氣通過軟管流了過來。我深深吸了一口,淡淡的實驗室氣味撲鼻而來,呼吸中混雜微量金屬與化學藥劑味,明顯不屬於道拉吉里,令人抽離。但這一吸,原本昏昏沉沉的我忽然感覺到肺部被填入了實體,慵懶的血液慢慢恢復活力,開始往全身淌流。我抬頭,驚訝地瞪大眼睛,「好像有感覺耶!」
我在氧氣面罩下模模糊糊地說了第一次吸氧的感覺,聲音像是拿個碗公罩在嘴上說話。「不是吧,我才開零.五耶!還沒真的開始嗨。我現在轉到一,你再試試。」說罷,阿果又轉了半格刻度,讓氧氣流量來到每小時一公升。在這個速率下,我的三公升氧氣瓶大約可以供應十小時氧氣,而連同今天拉卡帕背上來的一支,我總共有四支氧氣瓶,從此刻起吸到下山,綽綽有餘。
「哇!感覺都來了!氧氣好猛啊!」「對吧!八千米吸氧,效果比嗑什麼藥都猛。」元植笑著說。我十分同意他的形容,貪婪地吸著這生命的泉源、靈魂的燃料,每一個細胞都在大聲歡呼。
吸氧的感覺就像有一股能量沿著口鼻流入肺部,原本奮力吸氣仍接收不到氧氣的肺終於得以完全放鬆,不必再竭力呼吸,連帶整個人也放鬆了下來。獲得充足氧氣的心與腦開始恢復正常運作,手指腳趾不再冰冷,溫度隨著血液灌流全身,讓我漸漸暖了起來;思緒也不再亂成一團,說話開始變得有條理,可以講比較長的句子而不被喘息打斷。
我的疲憊如潮水退去,無力的眼神逐漸恢復光芒,不再呈現眼皮半闔的愛睏臉。只有在這種時候,才能感受到氧氣對生命而言,是何等重要、神奇的元素,就像在閉氣時間到達極限的瞬間衝出水面,讓人如插上快充般迅速回血。隨著狀態恢復,本來十分擔憂累了一整天,到第三營只休息四個小時就要開始衝頂會不會辦不到的我,開始覺得山頂是唾手可得的事。
原來,呼吸,是如此可貴;呼吸,就是生命的全部。這時,我不禁想起布農族的問候語「Mihumisang」,這句話的本意就是「好好呼吸」、「還有呼吸嗎」,也是好好生活的意思。此時此刻,光是能呼吸就是一種祝福了,不知道下山後,我能否一樣珍惜每一口新鮮空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