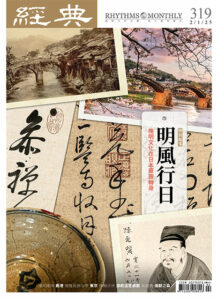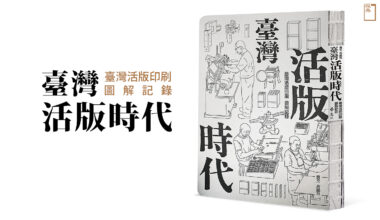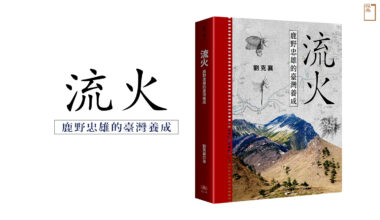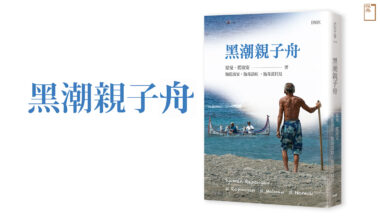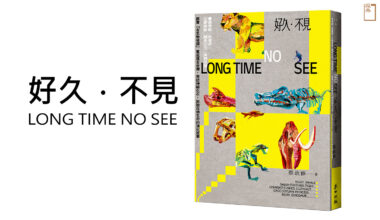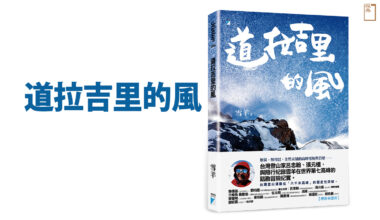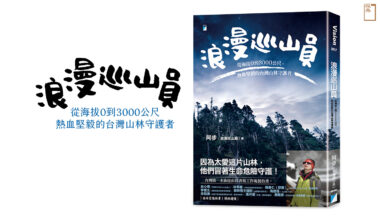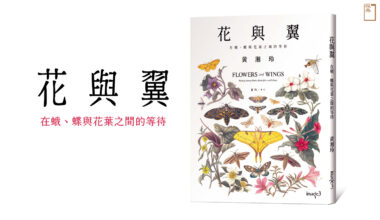我為什麼當野生動物獸醫師
最初的保育啟蒙
踏入野生動物救傷領域多年,每當為了野生動物在大太陽底下揮汗的時候,我總會想起奶奶的話:「漂漂亮亮的一個女生,為什麼喜歡和這些動物混在一起呢?」
我從很小的時候就立志要成為獸醫師,但其實自己也沒有料到後來會走上「野生動物獸醫師」這條路。
把我推向獸醫之路的狗
對動物很感興趣,我想是與生俱來的個性。小時候養過一隻名叫白雪的白文鳥,無論我在家裡的任何地方,只要一吹口哨,牠都有辦法立刻飛到我手上。還有一隻叫旺來的月輪鸚鵡,養了一陣子才發現牠是母的,而且很愛我爸爸。我們恍然大悟,難怪只要媽媽一出現在牠的領地便慘遭猛烈攻擊。原來牠視我媽為情敵。其他從小白鼠、魚、寄居蟹、蠶寶寶到小雞等,都曾經在我的兒童時期短暫出現。
八歲時,把我推向獸醫之路的那隻狗出現了。爸爸帶回一隻從路邊撿回的白色貴賓狗,醫師檢查得知三、四歲的牠體重只有兩公斤,可能是因為在外遊蕩了一陣子,大大的頭,配上一具非常削瘦的身體。我們為牠取名叫吉利。
我每天放學回家,快到家的巷口時,遠遠地便看到奶奶帶著吉利出來散步。我一喊:「吉利~」牠就以最快的速度飛奔來到我身邊。吉利最喜歡膩著我。
牠生病時,我便跟著爸媽帶牠上獸醫院。在一旁觀看著醫師從容地問診、量肛溫、做檢查等,加上回家餵藥後,病情都會好轉,讓我開始對「獸醫」這個職業產生好奇。
不過狗的壽命比人短,老去的速度快得令人感傷,最後促使我下定決心念獸醫系,其實也包含了想要為吉利做些什麼的心意。只不過獸醫之路並不順遂,升大學的第一年落榜,第二年重考時,填了三所獸醫系及一所工業設計系,偏偏錄取了工業設計系。我無奈地心想,或許自己真的跟獸醫系無緣吧,於是不再堅持。
然而眼看著吉利逐漸衰老,我發現心裡還是無法真的放棄獸醫領域。大二時,毅然決定考轉學考,總算順利地轉入屏東的獸醫系。
我想成為真正能幫助動物的獸醫師
雖然我努力地朝著獸醫之路前進,但吉利生命的衰落不會等我。
念獸醫系的第一年,吉利十六歲。牠的腦部一直有不正常放電的情況,後來愈來愈惡化,最後變得不認得自己的名字,似乎也不認得我們。每天為了照顧牠,我爸媽也無法好好睡覺。
我們討論過無數次是不是該讓牠舒服地離開,不要再受苦。看著牠好像靈魂已經不在身體裡似的走著,牠是不是也很難過?但始終沒有人有勇氣帶牠去安樂死。放假回家時,我常常對吉利說:「如果你的時間到了,不要擔心我們,你就安心地走……」
大二時的二二八連假,留在學校的我一起床就接到家裡的電話。爸爸說:「我們還是帶吉利去獸醫院安樂死了,一切已經結束……」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至今唯一一次哭到沒辦法講話,當時真的感覺到心好痛!沒機會好好地和吉利說再見是我心裡很大的遺憾,直到現在,我的皮夾裡還放著十歲時和牠的一張合照。
因為吉利,我想成為一名獸醫師。因為吉利的離開,我想成為真正能夠幫助到動物的獸醫師。
野生動物救傷的啟發
念獸醫系期間,大部分同學傾向日後從事犬、貓醫療領域。但我認為犬、貓的市場大,將來要投入相關產業比較容易,為了讓自己能力範圍更寬廣,便將重心放在犬、貓以外的動物上,例如實習時不找一般獸醫院,而是選擇一家馬場去照顧馬。畢業後便進入私人動物園工作,正式展開與野生動物的緣分。
園區內大多是從國外進口的野生動物,靈長類區卻有一群為數不少的台灣獼猴,這引起我的好奇。我問保育員:「靈長類的種類這麼多,為什麼我們會飼養一群台灣獼猴?」
「這一群是過往救傷進來的台灣獼猴,政府沒有明確的指示,我們也不知道能不能野放,就陸陸續續養下來了,」保育員說:「這一養就養了十幾年,猴群陣容愈來愈龐大。」
不過由於獼猴的數量實在是過多,園區的收容空間已不足,經過與地方政府協商,終於將這群獼猴帶去山區野放。
野放當天,我們駛進深山,一直開到車輛無法再前進的地方,將十幾個籠子面向森林,一打開籠門,獼猴便迅速地奔出,立即消失在森林裡。
這是我頭一次參與野放。回程路上,我不斷地思考:被人餵養了十幾年,牠們知道要在森林裡面找什麼食物嗎?離開家那麼久,牠們認識在地的獼猴嗎?牠們會懂得要躲避人類嗎?
好多疑問如同獼猴飛快的身影湧出。
那時因台灣能查到的資料有限,我開始搜尋國際上與「野生動物救傷」有關的資訊,第一次認識了「Wildlife rehabilitation」這個職業。字面上的意思是「野生動物復健」,但內容包括醫療、照護、野放訓練、野放及安樂死等,如何正確地幫助因傷病入院的野生動物再度回到家鄉的程序。
我想或許是受到獼猴飛奔離去的背影吸引吧,那是除了自由之外,身為野生動物該有的樣貌。而不是被限制在人為環境中生活,即使再美也終究是人造。
這應該是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對於某些動物來說,卻是最奢侈的事。
尋求生命的平衡交會
我開始對野生動物救傷這個領域感興趣,申請至美國明尼蘇達州的野生動物復健中心進行短期訓練。短短一個月,卻讓我真正了解如何從「保育」的角度,來決定動物的治療策略,並深植在我的心中。
舉例來說:面對感染了寄生蟲而出現神經症狀的野兔,獸醫師考量野兔的數量龐大、治療的預後不佳,加上有傳染可能性,因此只要是有類似臨床症狀的野兔,就會進行安樂死。
身為獸醫師除了救生,也身兼保育之責。考量因素還包括組織運作的整體資源,與其糾結在將每一個病例治好,更應該著眼大局,把資源放在康復機率高的動物身上;但只要動物有康復的可能,便會仔細地擬定不同物種的野放策略。例如過境的黑嘴天鵝,就算牠們康復了,仍須等待同伴經過時再野放,才能讓牠們趕上族群,避免單獨在外迷路而增加遇上危險的可能。
這種種努力都是為了讓重新回到家鄉的動物能夠做足準備,面對嚴峻的野外環境。而這樣的物種延續,也會為我們維持這片土地的平衡,讓人類能夠有好的環境生存。不只是為了我們,也為了我們之後的每一代。
野生動物保育不追求零疾病、零利用、零介入,而是在所有的動態中找尋平衡,甚至就連平衡本身都是動態的存在。
全台灣到底要多少黑熊或石虎才夠?沒有人有標準答案。但是讓給牠們多一點點生存空間,也許下一次的天災不會有那麼嚴重的土石流或淹水。這就是一次平衡的交會,無論用於保育或是個人的生命哲學上,我認為都非常適合。
或許正是「野生動物獸醫師」這份行業讓我找到人生的平衡,才能夠在這個交會點上持續地努力。
如何麻醉一頭獅子?
最瘋狂的麻醉計畫
治療野生動物的時候,麻醉是很重要的。牠們不像家中的寵物馴養,也不如犬、貓與人類之間親密、信賴,若沒有經過完善的動物訓練或麻醉,強迫進行某些醫療,往往會傷到動物及獸醫師自己。因此肉食動物如獅子、老虎都必須進入完全的麻醉狀態,才能確保彼此的安全。
頭幾回麻醉獅子時,前一晚我都會失眠,不斷在腦海中模擬整個流程──包括逃生路線。儘管我們是利用一種特製的電動壓縮籠能將獅子固定好打針,但麻醉危險動物,從逃生路線到逃跑的順序都必須事先擬定,否則意外發生的當下爭先恐後,只會阻礙逃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