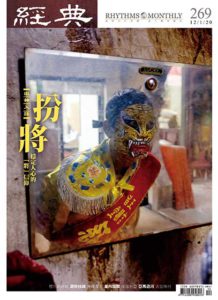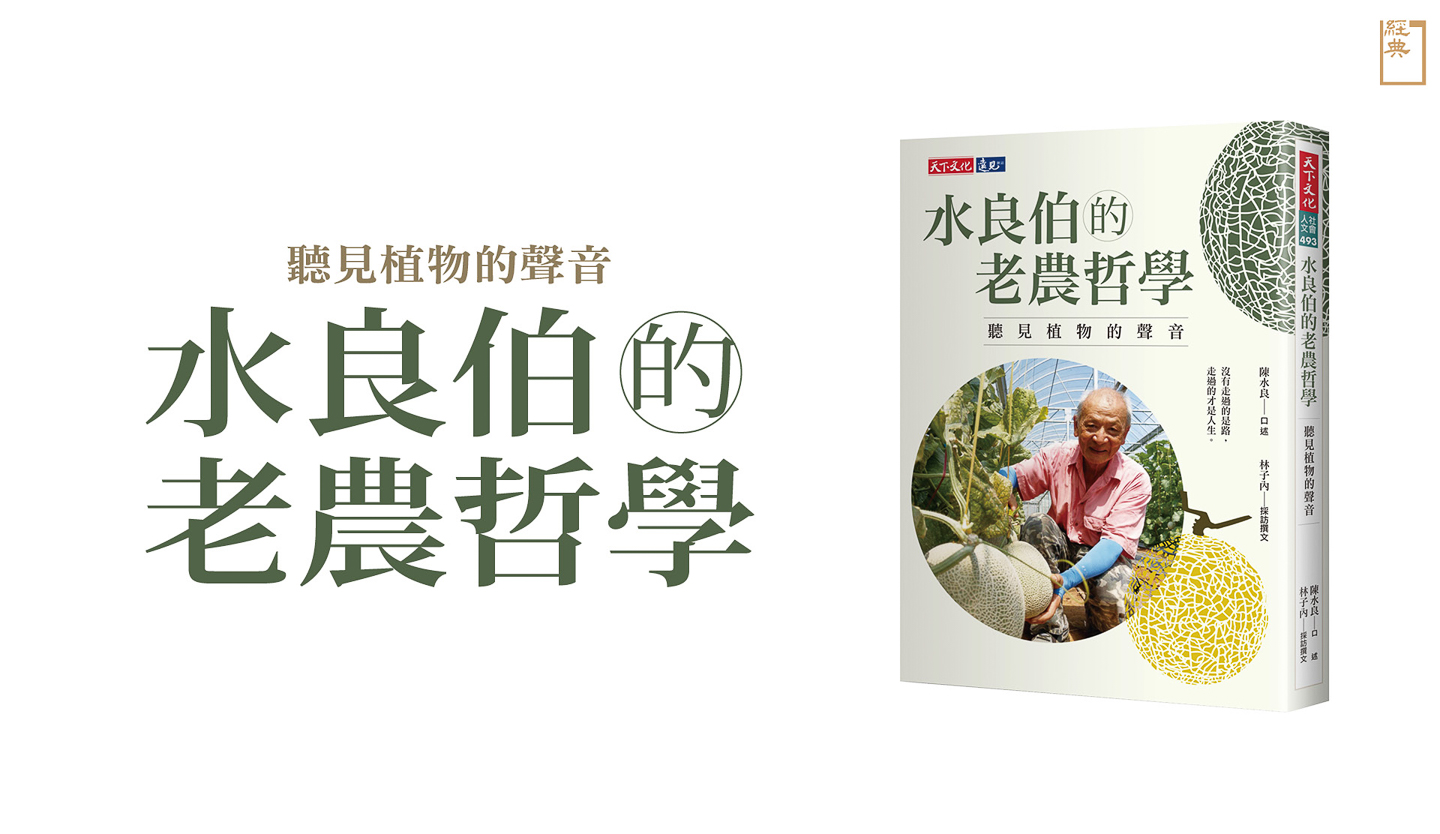建築師是魔術師,是夢想家,也是實踐者。為世人造景也造境。
建築的理性與感性
走進細雨霏霏中的松園別館。
「你看這黑松多麼美呀!」相較於妻子李綠枝的理性,甘銘源顯得感性許多,多數設計案都是憑著感覺接下。走在當時鋪下的木棧步道上,他說,當初就是因為喜歡這個環境,才會想要接下這個案子。
從松園二樓登高外眺,一眼望見美崙溪匯入浩瀚的太平洋,背後則是中央山脈與美崙山,即便是陰冷的天氣,也另有一種優美的場所精神。
松園的前身原是花蓮港陸軍兵事部,建於一九四三年,在荒置了超過半世紀後,交由建築師重新注入生命力。
主建築正面採原貌修復,但二樓原是宿舍空間改成展場,甘銘源不著痕跡地在屋頂開了四扇玻璃天窗,自然採光、通風佳。另一處木構澡堂,牆面被打開,借景一旁的生態池,成了藝文聚會及詩歌發表的最佳場域。李綠枝說主建築的木結構本身就很迷人,在修復過程中,把原本藏在天花板裡的屋架打開,讓原來的空間能量傾洩出來,呈現老建築應有的新樣子。
曾在日本設計公司象集團工作多年的甘銘源,在材料、構造工法上有扎實功夫,而曾在台大建築與城鄉基金會工作的經歷,讓李綠枝可以觀待整體環境,看到建築背後使用者的需要,超越建築人的思維,看到更寬廣的方向。
利用建築空間做社會實踐
建築是兩人想要對社會發聲的語言,畢業五年後開業,而後成立了大藏聯合建築師事務所,執業接近三十年的時間,從宜蘭移居雲林,在進行公共建築設計、文化資產修復、民居設計之間,他們都說了哪些「話」呢?
兩人成名其實蠻早,從初試啼聲的西寶國小即獲得台灣建築首獎,之後在九二一校園重建的育英國小也榮獲遠東建築獎項,但若以知名度來論,似乎又是建築作品有名,但建築師卻是隱形人。兩位建築師常說:「最好的作品是常民喜愛的生活場域,不必記得建築師的名字。」
譬如在台東前後花了十年完成五個精采的火車站,彷彿改造後的車站是從土地裡長出來那樣,讓人覺得親切。一般人不會特別去說這是 XXX 設計的,作品完成之後,這個車站就變成當地人的車站,主體就是使用者。這點功夫很了不起,設計者不居功,成為真正的公共財,讓車站成為全民的集體記憶。
車站是離別、重逢、相聚的場所,訪客造訪當地的第一印象,特別在花東地區,更是重要的對外門戶。池上火車站,以穀倉意象及木結構打造了具有池上米鄉意象的櫥窗,除了備受好評,使用滿意度也爆高。而這背後其實還隱藏建築師為堅持理念的一段折衝。
李綠枝說,池上車站原定規畫是北移重建,但建築師覺得市街和原有車站有密切關係,一旦移位,很擔心老聚落元氣大傷,於是他們與當地居民及業主鐵路局溝通,得到原地改建的共識,克服系統機房不可遷移的困難,最後以設計專業(一個大木盒子包住機房)贏得居民與業主的信心,成功地保留了池上人的記憶與文化。
花蓮太魯閣國家公園境內的西寶國小則是他們承接的第一個公共建築案,由於受到當時教師群對教育的熱忱所感動,他們有了更深度的參與,從原本預定的宿舍工程,擴展到整個校園的改造,他們依照當地的地形及揣摩開放教育的空間特性,發展出六角型簡約的單元空間。建築對他們來說也是一種社會實踐,利用建築專業,帶給教育現場更多的學習趣味與可能性。
想不到這個位處偏鄉的處女作卻意外地獲得了台灣的建築大獎,當時兩人才三十多歲,突來的榮譽,倒沒有讓他們沖昏頭,「因為喜歡才會去做,只要是有意義的,就會全心投入。」甘銘源理解到,硬體設計得再精采也還是需要軟體(師資與理念)的蘊含才有意義。
因為認同華德福的教育理念,在宜蘭他們投入了慈心華德福學校學生活動中心的設計工作,塑造了一個表演者和觀眾相當親近的表演空間,成為以戲劇來整合課程的華德福學校的核心場所。南遷之後李綠枝也將華德福教育引進雲林,在體弱多病的么兒過世後,兩人昇華對孩子的愛,成立利仁基金會,持續推動大環境裡的教育改革。
追尋雋永的建築
踏進南投埔里黃宅,前院是奇花異草的庭園,中庭布置水景,後院則是業主醉心的盆栽祕境,從門樓開始,花園、中庭、到後院,每一進都有自己的特色與功能,空間層次豐富。業主黃泗山是一名退休的國文老師,沏起一壺清香的春茶,與甘銘源就像老友一般聊起了重建時的趣聞。
甘銘源、李綠枝與黃家結緣始自九二一地震,當時建築界發起新校園運動,建築師們協力受災嚴重的區域重建,兩人從宜蘭繞過半個台灣,來到受災嚴重的埔里進行育英國小的校園重建,而因為在黃宅的借宿因緣,大藏建築團隊也承接了黃宅的修復與重建工作。地震後,很多老宅修不起來,有的因為子孫已經不住在那兒、持分複雜,從情感面、經濟面都無力修復;然而書香門第的黃家一直維持著古厝的質樸,與花園的芬芳,地震後他們堅持將正身原貌修復,為後代子孫留下文化資產。
過程中建築師不厭其煩地與黃泗山一家人耐心溝通,雖然曠時費事,但卻也因而建立了彼此深厚的友誼。「震災發生之後,我們的經濟真的是捉襟見肘,但好在建築師在建材或設計上,都處處為我們著想,感受到他們的熱忱與真心,之後就信任地讓他們放手去做。」黃泗山至今仍十分感念建築師的鼎力相助。「我們沒有米啦,只能分一些雜糧給建築師用,作我們這個案子,他們根本就沒有賺到什麼錢。」「但是賺到一個可以聊天喝茶的朋友啦!」 甘銘源開心地接話道。
「一個保存老宅和營造新住宅的融合經驗,我們一方面保留三合院的韻味,護龍改造為擁有較多半戶外的新空間,並內斂地在老護龍後方林子,延伸出新的合院住宅。」李綠枝如此做結。二十年後,重新再來檢視當時的作品,竟像丈母娘看女婿,愈看愈有趣。而在歷經時間的淬練之下,日日居住其間的人,更能感受建築的溫潤與設計的巧思。
甘銘源、李綠枝兩人也很慶幸,新住宅與老合院的修復重建,設計得恰如其分,建築師沒有「做過頭」。
另外一座位於海外的加拿大傳燈寺僧寮,則是突破完全仿舊的中國寺院套路,考據當地民情、融合北國島嶼地景,以西式工法構造,融合東方意象的修道場域,手法節制又不失力道。這樣在新建築中深藏典雅的文化意境,是甘銘源、李綠枝心中恆時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