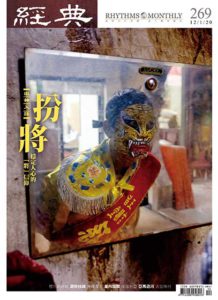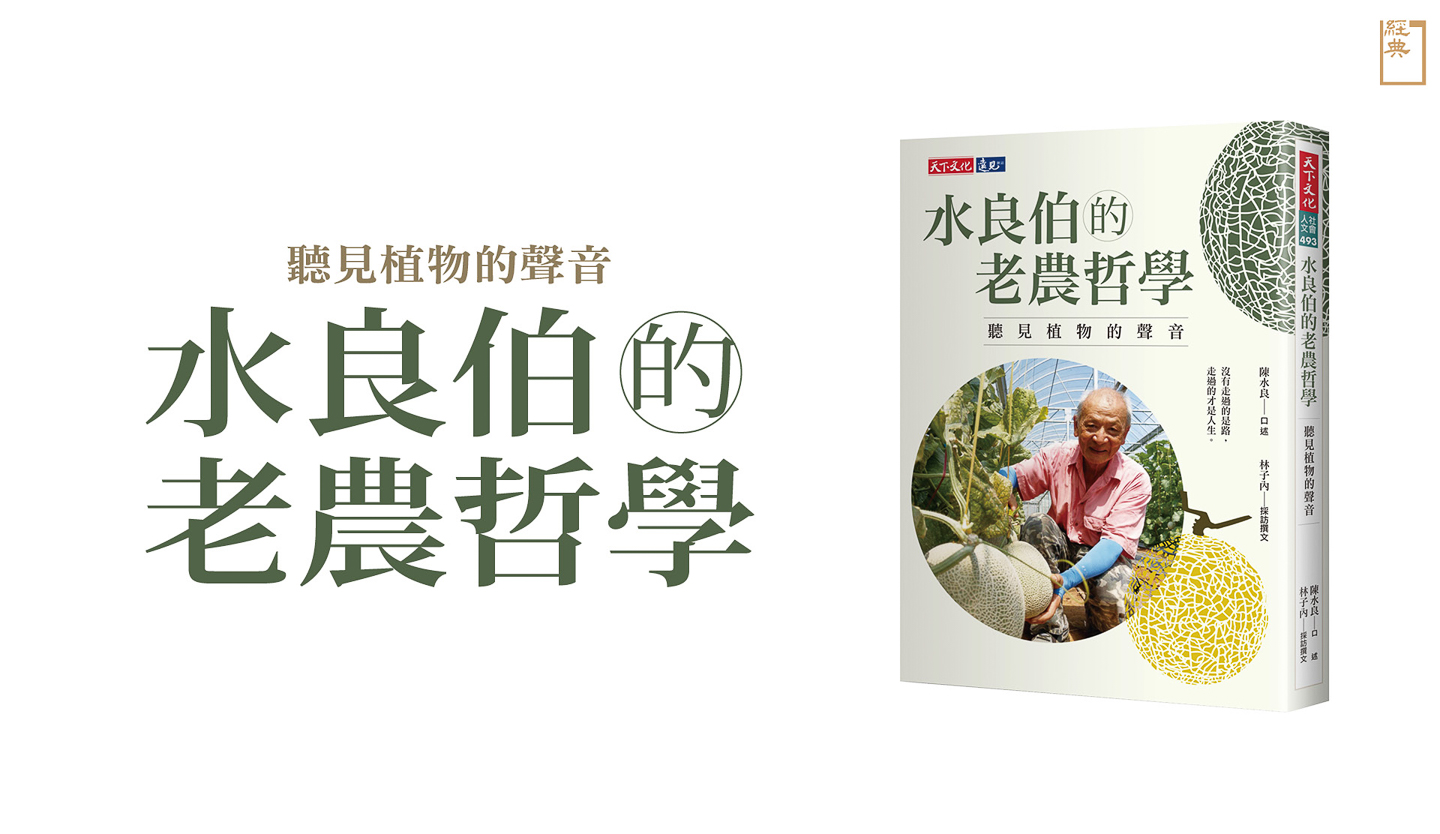東北角龍洞海底十公尺處,何欣茹嗆了水,死亡陰影強烈襲來,有如九歲時被火車碾過的夢魘。她掙脫教練,快速划水上升。教練也立刻跟著冒出水面,冷靜地看著何欣茹說:「現在放棄,考試就結束了。」何欣茹想了一下搖搖頭,教練說:「好,那把眼淚擦乾,我在水下等你。」
雙腿截肢的何欣茹是身障潛水第一屆學員,她終於克服嗆水陰影,拿到潛水執照。不過她那時不知道,七年之後,一群學弟妹正急著找她重回當初考照的驚魂之地。
二○二○年因為疫情影響,身障潛水協會停辦第七屆招生,改為學員重聚的「回娘家」活動。本身也是聽障潛水教練的協會理事長呂家瀅,始終焦慮著出席狀況。因為各種原因,許多身障者不再下水,像是何欣茹最後就因為先生的身體不適,而婉拒了出席。打了一輪電話之後,協會夥伴們開始擔心,不知能否邀到十個人出席?
身障潛水難上加難
回到二○一四年,那時台灣拿到潛水執照的身障者,總數連十個都不到。也在這一年,立法院正式三讀通過聯合國《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施行法,宣布身障者跟一般人享有同樣的環境權利。監察委員王榮璋當時正擔任中華民國障礙聯盟的祕書長,他曾在電視上看到國外身障者下海潛水,文獻上也鼓吹潛水能有效提高身障人士的心理健康。王榮璋想,既然台灣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可否也來比照辦理?
障盟找到國際企業願意贊助志工和經費,但最大問題卻是找誰來教?台灣雖然擁有許多很棒的潛點,潛水環境卻不友善,一般潛水員下水還得背負超過二十公斤的裝備通過各種崎嶇險路,身障者要怎麼辦?潛水環境乍看沒有空間,業者也諸多冷嘲熱諷,還好這時障盟找到了潛水教練陳克誠。
陳克誠是CMAS潛水系統的三星級教練,算是教練的教練,學生們都叫他「教頭」。
當了三十年潛水教練,太太曾因腰椎受傷坐過幾年輪椅,陳克誠因此對身障者並不陌生,他評估應該可行。不過陳克誠沒有評估到,身障者有許多不同的類型。
台灣第一次辦理「身障潛水」活動,除了參考國外文獻,也請國內潛醫科與復健科醫師參與。報名者要通過二階段甄試,最後面試由醫師與教練對障礙程度作評估。
報名的人很多,但是浮現的問題更多:聽障者戴電子耳防水到多深?脊損可以背著氣瓶下水嗎?玻璃娃娃來報名,可以收嗎……?
一般潛水員操作器材,以左手控制潛水背心充洩氣,右手控制呼吸調節器。然而陳克誠在面試時看到有個學員,右手掌竟然長在肩膀上,也就是俗稱的海豚手。陳克誠當下心想,「這樣我要怎麼教?!」
志工付出無所求
盧孫惠婷可能是台灣第一位因為要手語翻譯而去學潛水的人。第二屆有十位聽障學員,惠婷負責協助手翻,「那些潛水專業術語很難翻譯啊!什麼BC、中性浮力等等。」雖然盡力翻譯,但聽障學員還是很難理解,動作一直做錯,在水裡不斷重來。
惠婷常常邊翻譯邊偷哭,一般人學潛水都不容易了,為什麼這些身障者要來自討苦吃?
「比起一般人,」陳克誠教練說,身障者學潛水有兩點特別困難:首先是好勝心太強,在水面上會掩飾自己的恐懼,不懂裝懂。第二是身體重心難以掌握:下半身癱瘓的腳會浮起來;缺肢的則是左右無法平衡,肢障潛水者各自都有其困難點。
劉政奇從小喜歡貼著水族箱看熱帶魚。車禍癱瘓下半身之後,看到潛水招生很心動,但心裡害怕,又怕麻煩人家,掙扎了四年才報名。雖然成功錄取,不過他跟許多同學一樣,直到出發去參加營隊時都還瞞著家人不讓知道。
身障潛水營隊歷時五天四夜,學員要在這期間通過筆試跟術科測驗,再到海裡進行海洋實習,通過之後便能拿到初級OW開放水域潛水執照。好不容易來到訓練基地,卻有不少人第一天就想退出,「真的很可怕!」劉政奇說,要下水那一刻,才發現那恐懼遠遠超過自己想像!
身障者的恐懼跟障礙,也超越一般人的想像。陳克誠記得有位腦性麻痺學員,光是學會用嘴巴含住呼吸調節器,就花了兩天時間,而那只是一般人的舉手之勞。劉政奇有個同學也是脊損,體內的鋼釘打得比較長,軀幹無法挺直,在泳池裡上課都要靠坐在志工屈著的大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