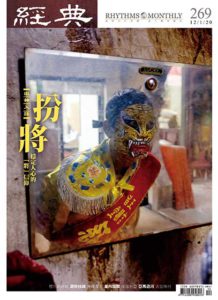俄羅斯的一首小詩《短》:
一天很短,
短得來不及
擁抱清晨,
就已經手握黃昏!
一年很短,
短得來不及
細品初春殷紅竇綠,
就要打點素裹秋霜!
一生很短,
短得來不及
享用美好年華,
就已經身處遲暮!
人生總是經過得太快,
領悟得太晚。
所以我們要學會珍惜,
珍惜人生路上的
親情、友情、同事情、
同學情、與戰友情。
因為一旦擦身而過,
也許永不邂逅。
詩很短,情很長;文很淺,意很深,像飽嘗風霜的老人,細數被浪費的無辜歲月;像洞見世事的哲人,在幽暗的人生路上點燃一盞泛黃的殘燈;也像長期浪跡海上的老船長和長期旅行的背包客,清楚海洋和陸上旅程的苦澀與甘甜,目睹那夜空繁星的閃爍璀璨。
有人說:年輕歲月長,年老歲月短。歲月似乎總是熱情地給年輕人較多的時間,卻也似乎冷酷地給年長者較少的殘年。因為年輕,感覺來日方長,錯覺有較多歲月存款,可以無度揮霍,對生命往往怠慢。因為年長,經過歲月風霜,留下塵垢滿面,鬢白如霜,自覺來日無多,已到風燭殘年,對生命的憶往難免慨嘆。
其實,時間鐵面無私,對待每個人都一樣。它公平地給人以出生,給人以童年,給人以青春,給人以年壯,給人以年老,給人以死亡,生老病死,時間永遠陪伴。站在人類有限的生命觀點,主客觀與因緣條件不一樣,壽命就有了長與短,但從宏觀的角度看,個人的壽命不論長短,都是稱為剎那,分別不出長與短。
時間的長短在心念和思想,要匆匆而過,還是仔細欣賞,決定一生的價值和貢獻。所以,在無限的時空裡,生命是短暫的過客,旅程都一樣。
但究竟時間是什麼?從哪裡來,又往哪裡去?大家都在分頭尋找答案。科學家和哲學家尋找的方向不一樣,科學家講實證,用物理的刻度找時間;哲學家講心智,用心靈的感悟找時間。
不少的智者都認為,時間與空間是一體的兩面,也就是說:時間即是空間,空間即是時間。一個是永恆,一個是無限;終極的本質都是「空無與寂靜」。只因人有感覺器官,有隱憂意識與潛意識,有生老病死,能感知花開花落,察覺斗轉星移,產生了時間、空間、人與人之間的相對概念。打破相對分別的概念,看透了,覺悟了時間沒有長短,空間沒有大小,回歸浩瀚無涯的宇宙本初裡,人的一生何其短暫,短暫得一轉身就是一輩子。
盛唐時期有位詩人叫張若虛,詩名並不怎麼顯赫,卻留下了一首千古傳誦的好詩《春江花月夜》。
夏昆在《最美的國文課——唐詩》一書中對這首詩的點評是:「巧妙運用四維空間,展現高超電影蒙太奇技巧。以詩歌探索時空哲學,解剖時間的有限與無限。」
這是一首見景生情,由情而發提問,由提問而深入反思,由深入反思而產生「移情作用」,感嘆生命新新生滅,人生代謝不住既短暫又漫長,既繽紛又空無,既虛擬又實有的意境。張若虛的《春江花月夜》一開始就這樣寫道: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
灩灩隨波千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
顯然這是在春天的某個夜晚寫的,這一夜的月亮是明朗的,帶了一點微風,作者站在江邊,目睹明月和春江相互輝映的共生共襯場景,對造物者的神奇力量以及自然的宏偉壯闊,觸發了文學的奇想。明月、春江、海潮、波浪,在空寂的朗朗時空中,共構忘我的唯美意境,詩人的意識流波裡,激起了極靜與極美的虛擬實境,在動與靜,水與月交會的剎那,變成刻骨銘心的永恆。
時空與其說是物理的現象,不如說是心智的產物,沒有心智感知的作用,沒有靜與動的相對性,就沒有時間流動的錯覺。所以,動與靜是時間,也是空間,因人而有,也因人而無;因人而同,也因人而異;是物理的,也是哲學的。如果沒有物質界的代謝現象,沒有人類的心智運作,沒有意識與心念的介入,那麼一切都歸於空無。
詩人總是多愁善感的,對自然界的時空流轉,總是敏感與細膩。張若虛緊接著用江流、月照、花林、霜霰、白沙,來描寫靜中之動、動中之靜,動靜在大塊運轉中,開始了連結與交會,開始了彼生我生,彼滅我滅,抒發了一種「萬物靜觀皆自得」的和諧詩趣。接下來的詩是這樣寫的:
江流宛轉繞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
空裡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
詩人把主觀的意識注入自然現象界裡,並賦予意義、韻律與詩境,是一種客觀情境的鋪排與主觀情緒的舒展,也為下一段的詩做預告。
江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
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
人生代謝無窮已,江月年年只相似。
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
詩人在詩中提出了一個驚人的大哉問:「江畔何人初見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皎潔的明月和澄寂的江水相互映照時,在江畔的人,是誰最早看到月亮的呢?而江上明月第一次照到人,又是什麼時候呢?人們都在猜想這個千古謎題,也都知道是永遠無解的謎底,儘管科學家殫精竭慮,哲學家苦思冥想,仍然跟謎底無緣。確實,剎那的有限生命,如何能解開永恆時空深邃的奧祕?
想要用短暫的生命一窺時空的無限浩瀚,就如同《莊子.秋水篇》所說的:「井蛙不可語於海者,拘於虛;夏蟲不可語於冰者,篤於時;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一樣。井蛙,受到狹小空間的限制,難以知道壯濶的海洋;夏蟲,因為夏天生,夏天死,受到時間的限制,難以知道冰雪封地的冬天;不能真知卓見的讀書,因為受到教條的限制,難以知道宇宙的究竟實相,儘管科學家勤於尋覓,哲學家勤於苦思,文學家勤於遐想。
年輕人把希望寄望於未來,年老人將回憶置於現在。歲月不斷推移,希望成了回憶,一生就在無窮的希望和無盡的回憶中悄悄點滴錯過,又有多少人能把握如今現在?
「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孔子感嘆時間如江水,不停流逝,時間滑溜溜,從來沒有人能抓得住它。但細細想來,我們每個人又似乎都是時空洪流裡的一介微塵,一小滴微不足道的水,從沒有離開過時空,部分不知道整體的可貴,一寸光陰一寸金,歲月如流金,多少人能夠體會?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新新生滅,代謝不住,日起月落,四季推移,自然法則,維繫人世間生滅的平衡,如果自然法則被打破了,世界也就不存在了。所以,不要蹉跎,不要感懷,只要活在當下的每一分、每一秒,每個剎那,時間沒有長與短,人的生命應該追求永恆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