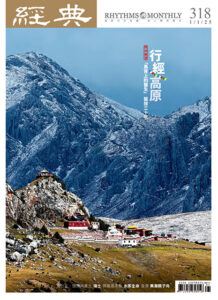我擺脫陰霾,十一月底全台秋高氣爽,從北到南很多地方都在周末熱熱鬧鬧辦活動,包括高雄杉林。
一長串人龍在大愛園區大草原間行進著,這已是第五年全杉林區健走活動,住台二十九線大馬路對面的上平、附近月眉和新庄等社區居民也在隊伍當中,老老少少三百餘人。穿越草原、永齡農場,經隔壁的小愛小林村,再循省道走去兩公里外的日光小林村門口後折返。
日光小林、小愛小林與杉林大愛園區都是莫拉克風災後,由紅十字會和慈濟慈善基金會分別在台糖土地上,以社會善款和民間志工等資源,協力完成給災民容身安居的組合屋;同時,在小林村附近的高地上也依原先村莊樣貌重建五里埔社區,將重傷的南沙魯(那瑪夏區),和完全滅村的小林村(甲仙區)居民給優先安置好;至於同被劃為危險地區不宜居的南沙魯上方另兩個村──雅瑪、達卡努瓦,以及荖濃溪畔南橫公路沿線的桃源、寶來、六龜等居民也可申請入住。
面對漫天遍野的黃泥土石,片瓦不存,此情此景即便不捨,也不得不捨。
南沙魯唯一的農夫
初冬的清晨,楠梓仙溪在陽光下閃閃發亮,顯得格外清澈,它灌溉了翠綠的山林卻也蠻悍的刷洗裸露出惡地。
站在南沙魯此岸生薑園裡四十三歲的李昊,是近十年來每天上上下下往返於大愛村與老家的「專職」農夫,「很難想像,河面原本十米寬,莫拉克一下子就把它沖成兩百米。今年先後兩個颱風,尤其前一個凱米,把我的地整片沖走。」原來李昊腳下還有好大一塊地,現在留下幾叢灌木,成了河道的一部分,這不過兩個月前的事。
黝黑的臉龐、褐色的瞳眸定定地看著,十足布農族獵人與農人的堅毅,「河道一直在變,之前靠對面的麻竹林,現在愈來愈向這邊了。」李昊指著對岸的竹林,努力想讓我們明白這些年的變化,「我想往上開墾,看有沒有誰願意放給我做。」言語中帶著妥協,李昊心裡很清楚,上天隨時會把腳下這片地再收回去。
這個季節收成生薑、芋頭還有四季豆,不過都一年一收,李昊說他還得種點別的,如:短期葉菜、玉米。以前他隨便種,不管有沒有經濟效益,久了,漸漸知道要間隔或交替種點別的,他也有水蜜桃和芒果樹,「如果上午這塊地做不順,下午就換去另一塊,這是一種調劑,轉換心情。」過程中的挫折就這樣跟自己、跟土地對話而化解。
當初隨著家人遷去杉林,老婆肚子裡懷著第三個孩子,倉皇中生下了大愛園區第一個寶寶,給新厝添喜,如今十五歲讀高二了。
那瑪夏區的布農族人都被安置於大愛村同一區,哥哥們就地做傳統族語工藝教學,但李昊喜歡山上的自由自在,選擇回老家耕種,常跟在身邊玩土扒地的是最小的兒子,念小班。他生養了五個孩子,近年,太太罹癌,人生一再波折,讓昔日嚼檳榔喝酒當板模工的李昊,漸漸變得謙卑,懂得思考,他現在勤勞而有責任感、戒除菸酒檳榔注重身教,話語中充滿智慧。
巴楠花 無處不開花
原名民族村的南沙魯里,是原來三民鄉(後改稱那瑪夏)三個里中的一個。位於鄉公所和衛生所上坡的民族小學,是二○○九年第一個被堰塞湖潰決,夾著大量土石給覆滅的建築,主要街道兩旁房舍無一倖免,校長張新榮(族名阿浪)帶著師生遷來大愛村復校,改名巴楠花部落學校,李昊幼子念的就是這間。
校門口一大叢一個半人高的巴楠花(五節芒,布農族語Padan),在深山野地到處可見,保育水土且生養眾生,可蓋屋頂、砌牆、編結做記號、藥用、當野菜或祭祀用,用處很多;阿浪校長解釋,它再生力很強,根不怕火燒,校名巴楠花正象徵八八風災後失根的族人生命強韌,異地重生。
早上七點半,高年級學生在校門口燒起木頭,這是每日的祭儀,日落時灰燼猶有餘溫。
從幼兒園、小學部到中學部,二○二五年將有高中部,這是一所全人實驗學校,學生當中有七成原住民,三成為認同原住民文化的漢人子弟,自旗山、美濃,甚至更遠的屏東跨區就讀。它不同於一般學制,依照小米生長季節將一學年分四個學祭:春學播種祭、夏學射耳祭、秋學進倉祭、冬學年終祭。阿浪望著教室周圍高大的楓香說:「很簡單,我告訴孩子們,只要枝頭冒出嫩芽,就是小米播種的時候了。」
草地正中央以八根漂流木做柱子,搭起圓形的迎賓台,象徵八部合音。
週五社團課,二年級的孩子在族語老師大亥(Dahai,漢名:李聰明)指導下,兩人一組,一人抓頭一人拖尾搬芒草,個頭小就只能做這些,五、六年級個子高的則攀梯子爬上屋頂覆上巴楠花,搭茅草房,「原本住在山上受自然養育的族人,一旦離開土地,生活在主流社會的邊緣就會沒自信,到底我們還剩下什麼呢?現在的都市生活讓族人經驗不完整,應該讓孩子從小在校園中找回自然經驗與判斷。」校長張新榮思考著。
他自己也在都市生活多年,多了幾分歷練,接任校長後,帶領多數是漢人的老師接軌原住民文化,找回合時宜的布農傳統,設計出一到九年級深淺不同卻按部就班,彼此銜接的課程。即使離開原鄉,他也要讓布農文化落實到現代生活中。
同舟一命 日光小林生機迸發
在大愛園區不遠處,有九十戶人家的日光小林,住的都是昔日小林村人。早年他們半數是清朝時期隨官兵開山撫番,從北部桃園、新竹或南部旗山、美濃來伐木採腦的客家人,另一半則是玉井南化東來的平埔族「大武壠社」群,他們信仰阿立祖,完全不同於漢人和布農族人的信仰。因此日光小林村沒有教堂、宮廟,而是搭起公廨做形象標誌,每年大武壠祭,族人都回去五里埔夜祭,一起祭拜番太祖,十五年來都如此。
七十六歲的徐吉綠搬下山來儼然國寶級藝師,他從小跟著父兄打獵漁撈,很會編魚笱、背簍,家門前一只一人高的魚笱就是他的作品,將一支刺竹竿削成八等份,邊彎曲邊綁藤皮,由窄小漸寬的裂隙完全符合現代生態工法,只捕大魚放走小魚,目前五里埔公廨、小林平埔族群文物館中的魚笱都出自他巧手,問編一個多久時間:「兩小時。」他輕鬆回答,指著前方的樹林,就地取材。
八八風災前,小林村已少有人用傳統魚笱捕魚,災後因入住日光小林村的年輕人居多,長年在都會區工作,危機中凝聚大武壠文化意識,而成立自己的協會,很積極辦活動、做傳承,把黃藤和竹子都種進了自家院子,展現劫後再生的力量,企圖心更勝以往。
織著故鄉記憶的魚笱成了徐吉綠和年輕人的慰藉,也讓外地人有機會聽聞大武壠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