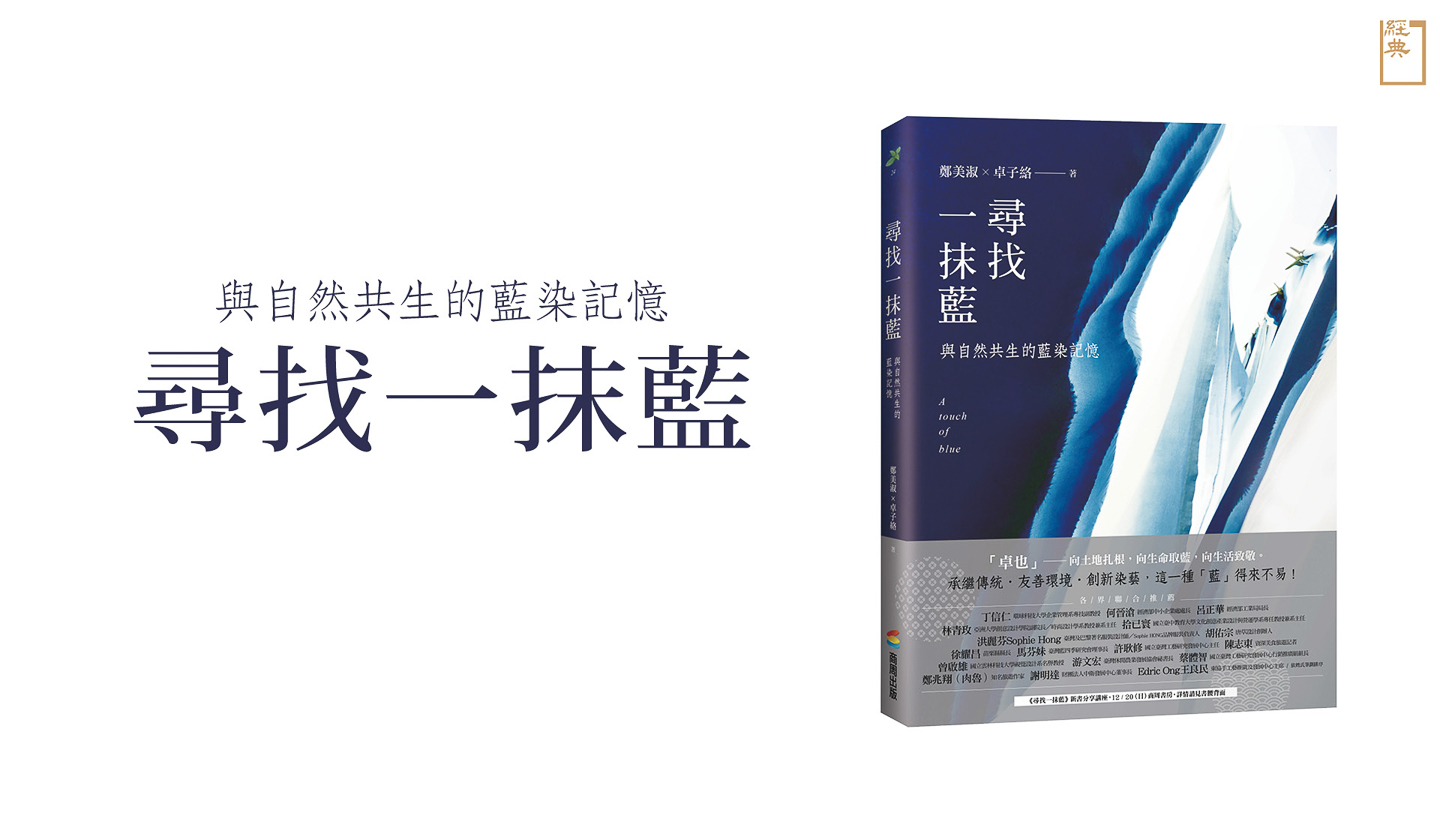猶如流動的銀河,當數以千計的小小銀鱗鯧在人造光源的照耀下,反射出夢幻般的光芒時,站在巨型水族箱前的遊客,莫不發出一陣陣驚嘆。當海葵魚、裂唇魚、豆娘魚、灰貂鯊等四處穿梭,與拖著長長尾巴的魟魚一同優游時,許多人的手機快門,更是一刻也沒停過。
這裡是台灣北部的某一水族館。受疫情影響,雖說遊客至少掉了九成,但肯在假日花錢買票進場的民眾,還是大有人在。只是在半年前,該館在開幕之初,就因魟魚受傷、水母觸手打結、企鵝頻撞玻璃,以及海豹活動空間過小等問題,受到不少人質疑:這樣的空間,真的有寓教於樂的效果嗎?還是對於第一次接觸到海洋生物的小朋友來說,從此他們心目中的海洋,就只是那一方藏身於水泥建築內的水族箱?
事實上,除了世界各地的海洋娛樂機構如海洋世界等都有過相同的爭議外,即使是向來最傳統的海洋教育機構身上,也不乏有類似的狀況;二○一四年間,位在屏東的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簡稱海生館),有高達七尾的鯨鯊因不適應人工環境而接連死亡,所謂海洋博物館的存在,是否為海洋教育必要之惡的說法,引發空前的激辯。
贊成的人說,一般人即使會潛水或游泳,也不見得有機會「一站購足」,能一次就看到那麼多的海洋生物;反對的人則表示,館方除了對動物的引進來源不夠透明外,海洋生物也有動物權,強迫牠們離開原生地,生活在人工的環境裡,本身就不人道。
但一如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館長陳素芬所說,博物館的設立,本在於提高其研究、保育與教育功能,「所以這些爭議,多半是管理上的問題,博物館的存在,還是有其價值。」陳素芬說。
只是台灣作為一個海洋國家,擁抱、認識大海,是再天經地義的事嗎,特別是如果我們親近大海的管道,只淪為以管窺天般的水族箱,那樣的方式,是不是反而只會讓我們與海洋的距離更遠,誤解更大?
「歸根究底,這都是台灣缺乏真正的海洋教育所致。」台灣海洋教育推廣協會祕書長郭兆偉,曾沿著海岸徒步環島高達六次。他表示,在他無數次的推廣經驗裡,常發現很多人小至對於餐桌上海鮮料理的名字,大至對潮間帶、近海與海底有什麼差異?又環繞島嶼的洋流有哪些等等問題,「大家不知道就算了,但如果還反過來問我,知道這些跟自己有什麼關係時,那就太誇張了。」郭兆偉感嘆,這也難怪台灣海廢問題嚴重,因為民眾極少接觸真實的海洋,對它就沒有情感,沒有情感,自然,也就不會覺得有保護它的必要了。
教育,反轉的關鍵
「所以台灣如果想坐大,只有透過喚醒血液中海洋DNA的作法,才能成為名符其實的海洋國家。」郭兆偉說。
但早在他與夥伴於二○○八年成立推廣協會以前,類似的團體在民間,只有以保護鯨豚為主的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行動較積極;在學校方面,則不管是號稱海運業的三大搖籃:台灣海洋大學、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現稱高雄科技大學)及台北海洋科技大學(前身為中國海專),或包括鹿港高中水產養殖科在內的九所高中職,它們雖然作育無數專業人才,讓台灣的航運業與遠洋漁業都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但對於改變一般民眾與海洋的關係,卻鮮少有任何幫助。
最後,連同一般的國高中小學,長期以來,也以國數理化等考試科目為主,海洋教育不只破碎,也淪為比配角更不如的龍套。
一個重大的轉折,來自於十二年國教的108課綱頒布後,國中小學的教育方針,從過去九年一貫國民教育的訓練基本能力,變為厚植人文素養;此外當「海洋立國」終於從口號變成政策時,「海洋教育」也從環境教育中獨立出來,成為學校選擇自身的特色教學時,一個全新的選項。
冬日的台南,難得寒風簌簌。來到這個全台首創「海洋教育輔導團」創始國小台南市西門國小時,教師邱馨慧先是解釋國民教育輔導團,是教育部行之有年的教學設計,作法是從各校裡找出對特定科目有熱忱的老師,大家一起研發教材,形成模組後,再提供給其他老師當參考。
「但在過去,各縣市都只有國文、數學、英文教育輔導團等,就是沒有海洋教育,西門國小會籌組海洋教育輔導團,全因為前校長莊崑謨的關係。」邱馨慧說,二○○七年時,當西門國小收到一批其他人不要的OP帆船時,考量校址就在舊日的台江內海上,附近的鹽水溪、漁光島與安平港,構成一個個平靜的水域和水道,怎麼說,都適合用來推廣獨木舟、OP帆船與SUP立槳等運動。
「再加上學校所在的安平是個歷史老城區,少子化嚴重,在這裡,連區公所的護理師都要上街宣導,鼓勵生育;所以如果學校沒辦出特色來,就可能會被裁併掉。」邱馨慧笑說。
於是在莊崑謨和當時還是主任的邱馨慧,以及已退休教師周宗明的帶領下,西門國小的小朋友,個個都有機會划船;為了深化他們對航行的認識,「划船之外,了解河川和海洋的上下游關係、潮汐的起落、湧浪的流向,都是深化的知識,教學的重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