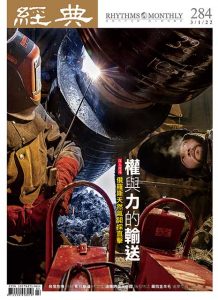五千年以來,蒙古游牧民族與蒙古大草原間保持著微妙的平衡。同樣身為必須克服惡劣氣候、逐水草而居的夥伴,牧民與羊群建立了堅不可破的羈絆。
蒙古的氣候屬於典型的大陸型氣候:溫差極大,夏季最高可達27℃,冬季則可低達零下30℃;每年降雨量僅有二十至三十毫米,而草原上颳的強風加上高溼度,讓體感溫度降至冰點。
在如此嚴峻的環境下,游牧這種結合食衣住行的生活型態,自然成了當地人主要的生存之道,也激發出許多充滿智慧的求生訣竅;以當地人的帳篷「gher」(或許說「蒙古包」更加親切)為例,根本是為這些一年起碼要搬家兩次的游牧民族量身打造,既輕便又靈活、易於搭建,且圓形的設計使內部更容易蓄積的熱量,以抵禦室外零下數十度的嚴寒,整個帳篷的空間都被利用的淋漓盡致。
然而,人類與草原間長年維持的平衡,在近幾十年內卻逐漸傾斜。在全球暖化的影響下,蒙古地區的氣溫上升尤其有感,上升的幅度約為地球其他區域的兩倍;而原本就偏低的降水量更是從上世紀中葉至今減少了10%,有20%的河流與21%的湖泊陷入長年乾涸的困境。過去約每十年會迎來一個特別乾旱的夏季與特別寒冷的冬季,而現在則變得更加頻繁,大量的積雪覆蓋在牧場上,動物們在飢寒交迫下大量死亡,損失數以百萬計。
被迫定居卻又破滅的首都夢
隨著蒙古政府放寬了境內兩千五百萬隻牲畜(包含綿羊、山羊、馬與駱駝)的數量限制,蒙古境內的牲畜數量暴增了將近三倍,其中經濟價值最高的喀什米爾山羊(cashmere goats) 的數量更是在二十年內翻了四倍之多。牲畜的暴增對環境造成傷害,覆蓋著蒙古約四分之三領土的大草原,如今已被缺乏管制的放牧破壞了將近七成;雪上加霜的是,為了尋找珍稀的水資源以用於民生與礦業,開發過程對環境造成了更進一步的傷害。
曾經壯闊的蒙古大草原,終究不敵如此凌厲的「攻勢」。從前無比茂盛,甚至能讓動物藏身其中的大草原,如今只剩下寥寥無幾的灌木叢淒涼地矗立著;草原的面積曾是德州的兩倍大,如今卻以驚人的速度變成沙漠;僅存的草種,也逐漸從原生種變成動物無法食用的外來種,這對牧民的生活無疑又是一大打擊。許多牧民不願再看到自己的牲畜餓死,選擇捨棄游牧生活,前往蒙古首都烏蘭巴托(Ulaanbaatar),為自己與孩子尋求更好的未來。
自一九九一年以來,蒙古的生產總值(GDP)每年以破紀錄的速度節節高升,直到二○一六年甫停止。政府於一九九四年通過一條法律,給予每位公民首都周圍零.七公頃的土地,可免費使用十五至六十年之久,此一政策吸引了無數牧民前往烏蘭巴托,便於移動的蒙古包再無機會發揮其易於搬遷的優勢,一座座的定居於首都郊區。
大量的移入,使烏蘭巴托的人口數暴增至將近一百五十萬人,這座占地僅為全國總面積0.5%的城市,卻容納了全國總人口的一半。這些新移民,平均收入僅為都市人的一半,生活品質顯得差強人意,烏蘭巴托也漸漸無法負荷日益增加的人口,因而無力提供這些移民基本的生活條件。這些地區的道路僅約一成有鋪設柏油路,學童連上學都困難重重;由於沒有裝設水電管線,當地居民不像從前在草原上靠焚燒糞便取暖,而是使用煤油、煤炭,若無法負擔這些燃料,便改以焚燒各種廢棄物,因而產生大量廢氣,加上工業與交通廢氣的排放,讓烏蘭巴托儼然成了世界上空氣汙染最嚴重的城市之一。
即使全蒙古的人似乎都往首都湧進,但自從二○一四年起,有愈來愈多的牧羊人選擇反璞歸真,恢復以往的生活方式,或許是無法接受烏蘭巴托的生活環境,又或者是這場「首都夢」破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