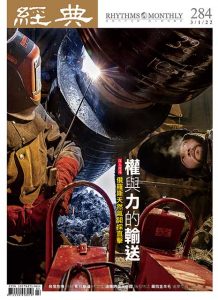一九九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晚上七點三十一分,隨著莫斯科克林姆林宮上飄揚的鐮刀槌子紅旗正式降下,蘇聯也在這一刻正式走入歷史,分裂成十五個獨立的共和國,其中包含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
這三個位於歐洲邊陲地帶的小國,在歷史上多次夾在德國與俄羅斯間無所適從,二戰後好不容易脫離了納粹的統治,卻成為互不侵犯條約的犧牲者,遭到蘇聯併吞,直到蘇聯解體、宣布獨立為止;如今,三個波羅的海國家亟欲在歐洲站穩腳步,但它們將再次面對野心勃勃的俄國政府。
除了軍火庫中形形色色的武器,俄國還有許多達成目的的方法,其中一種就是建立親俄文化。二○一二年時,拉脫維亞舉辦了一場公投,表決是否將俄語設為其第二官方語言,這場公投成功動員了許多俄裔人士,但最後仍未通過。另一種方式是干預媒體,俄國的電視台時常報導虛假或扭曲的事實,在俄語圈內灌輸人民「拉脫維亞、愛沙尼亞是反抗者」的想法,從而令人民對這兩國產生反感。除了以上兩種方式,俄羅斯為了施行擴張主義,還使用了混合戰爭技術(Hybrid Warfare),助長目標內部衝突,並控制其產生的動亂進而得利,近年較為著名的即是網路戰。
許多愛沙尼亞人對二○○七年的那場網路攻擊可說是記憶猶新,起因是愛沙尼亞政府準備拆遷首都塔林(Tallinn)的一座蘇聯紀念銅像,此舉引起國內俄國人的反彈,並開始攻擊國內銀行、媒體,甚至是議會等政府部門的網站,造成網站被迫暫時關閉,一連串的攻擊幾乎造成國家癱瘓。這種嶄新的戰爭型態震撼了北約與歐盟,因而在此事件後於塔林成立北約網路防禦合作中心(CCDCOE),並投入大量資源以培養成員國對於網攻的應對能力。
除了這些「軟實力」的進攻,俄國的軍事實力一直以來都極具威脅性,北約與歐盟成為立陶宛、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應對俄國邊境緊張局勢的得力盟友,美、法、德、英等國家皆有簽署的北約條約,一定程度限制了俄國的軍事入侵行動。
諷刺的是,另一個共產主義大國中國,也採取著類似的行徑,中國千方百計設法將台灣納入自己的懷抱,北京政府將這座政治分離的島國視為本國的一個省分,宣布獨立對北京而言就等於宣戰。
惺惺相惜 攜手對抗強權
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Vilnius)於二○二一年十一月,授權台灣成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這是台灣在歐洲首間以「台灣」名義成立的代表處。一直以來,受制於中國政府,台灣在國際上都只能自稱「中華台北」,理由是若以「台灣」稱呼這座島,似乎就像承認它是一個獨立的國家,立陶宛此舉,立刻讓其化身這場地緣政治風暴的中心點。
中國與立陶宛的外交戰因此揭開了序幕,並且愈演愈烈。中國首先召回了駐立陶宛的外交人員,隨後對立陶宛實施貿易禁令,並透過跨國大企業對其進行施壓。根據法國《世界報》(Le Monde)的報導:「作為與台灣交好的懲罰,北京正在對立陶宛,乃至於對整個歐盟,發動一場真正的『混合經濟戰』(Hybrid Economic War)」。
面對中國對立陶宛的孤立戰術,台灣人民選擇團結起來,用各種方式支援他們的新戰友。二○二二年一月上旬,台灣宣布對立陶宛投資共計兩億美元的基金,一周後又宣布將發放十億美元的信貸基金,以支持立陶宛與台灣公司間的聯合項目。
這不是人們頭一次為了反共產主義的壓迫而團結起來,一九八九年八月二十三日,兩百萬人手牽手,形成一條長度超過六百七十五公里、貫穿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的人龍,這場史稱「波羅的海之路」的和平示威行動,在國際上爭取了驚人的注目,進而促成了這三個國家日後的獨立成功。
《華盛頓郵報》報導:「這個波羅的海小國的勇氣,鼓舞了長年面對中國威脅的台灣人民,提醒了他們應該更積極地在逐漸由中國所主導的國際舞台上,爭取更多的空間。」這些國家提醒了我們,此時此刻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隨時可能陷入危機,野心勃勃的獨裁者們隨時都虎視眈眈,波羅的海諸國意識到了這一點,並努力捍衛著得來不易的自由。
回顧壓迫象徵 方知自由可貴
蘇聯解體、宣布獨立後,立陶宛政府立刻展開了大刀闊斧的整治;首先是罷黜共產黨,隨後禁止使用鐮刀、槌子、萬字符號(Swastika)等與蘇聯和納粹相關的符號,這些象徵只被允許出現在博物館中,以時時刻刻提醒人民它們曾帶來的傷痛,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也隨後跟進。波羅的海諸國並未選擇抹去這些歷史的傷痕,而是直面它們,每當看到它們,就會想起自由是多麼得來不易。
格魯塔斯公園(Grūtas Park)坐落於維爾紐斯南部,靠近白俄羅斯邊境,這座公園建於二○○一年,安置了許多波羅的海地區被拆除的前蘇聯雕像,走訪格魯塔斯公園,宛如走進時間隧道,並展開一場漫步於共產時代的立陶宛的教育之旅。格魯塔斯公園記錄下立陶宛歷史中悲慘的一頁,它的創立引起強烈的反對,直至今日仍充滿爭議。
蘇聯碉堡(Soviet Bunker)是另一個紀錄歷史傷痕的景點。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Brezhnev)為了應對與美國間可能發生的核戰爭,於一九七八年下令於首都近郊建造這座碉堡以作為觀測所。遊客可在冷冰冰的碉堡內,體驗當時政治犯被關押於集中營的感覺,換上囚犯的深色夾克,在聽完一場頌揚社會主義的演說後,走上俘虜的道路,準備在地下陰暗潮溼的KGB辦公室中接受審問,陰沉的衛兵與德國牧羊犬的吠叫聲,都令人心生恐懼。
在鄰近立陶宛北部波什埃村(Plokščiai)的森林中,坐落著波什汀導彈基地(Plokštinė missile base),蘇聯曾在這裡部署過驚世駭俗的R-12彈道導彈,這種導彈同時也是古巴危機的主角。二○一二年,這裡開設了冷戰博物館,遊客可以參觀現有四個筒倉之一,以及冷戰時期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