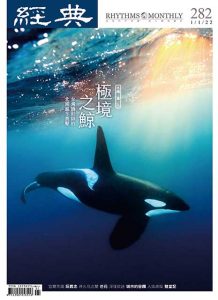人物傳記作為人類歷史的一種內涵,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歷史就是記敘人的事,歷史所本的有官方正式紀錄,也有民俗敘事談說,其中自有對人作記敘的傳記。我們歷史上傳記起源甚早,司馬遷《史記》中就有《列傳》,其他文明也有人物傳記,近世以來由於科學的影響益彰,創造科學的科學家的傳記也就蔚然興起,著作不少,也引起社會相當普遍的興趣。
我因為從事科學新聞工作,因緣際會地寫了兩本科學家的傳記,對於這件事有些經驗,也有一些反思。我是一九八九年到紐約一年,正式開始進行《吳健雄傳》的訪談和資料研究蒐集工作,那時我認識吳健雄超過六年,做科學新聞工作也超過了十年。
雖說對於吳健雄和物理都有一些認識,《吳健雄傳》的寫作比起原先所想的,還是困難許多,其中原因甚多,簡單說就是資料蒐集的範圍以及資料採用的選擇,都有客觀能力與主觀價值決斷的局限,不可能盡如人意,當然也與我初做此事經驗不足有關。整個計畫除了在紐約一年的密集訪談和資料研究蒐集,後續還有些訪談以及其他來源資料的蒐集,回到台北因還有新聞工作,因此寫了七年才完成。
雖說《吳健雄傳》確實是言必有徵的一本傳記,楊振寧的推薦也說「為此類傳記書開一新紀元」,嚴格講不能算是一本最理想的傳記,我自己的檢討,就是經驗不夠,對於傳主的挑戰和穿透性還有些不足,這當然就牽涉到對於傳記的價值定位問題。
《吳健雄傳》可說是個有點「初生之犢不怕虎」的計畫,嘗過虎威的小犢總是學了教訓,對之頗有懼畏,沒想到兩年後,我居然再開始了一個新的傳記寫作計畫,這其中有許多道理,不是此文的重點,不在此說。新的《楊振寧傳》寫作計畫是一九九八年開始,也有一年在美國就近與傳主與相關人士訪談,及一些資料研究和蒐集,回台灣後再經過三年的寫作,於二○○二年出書。《楊振寧傳》寫得稍快有幾個道理,較有經驗是其一,另外寫作的後兩年時間,沒有工作的全時寫作也是因素。
《楊振寧傳》可以說是一本比較成功的傳記,得到較多肯定,自己也比較滿意,除了楊振寧的科學成就與社會影響層面比較深廣,另外面對傳主的詰直挑戰、資料的認知穿透,因為有前一本傳記寫作的經驗,能夠做得更加深入,傳記的整體價值與可看性,也就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