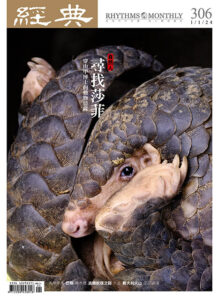許多人將當前政府支持科學研究的模式視之如常,但是如果以近代科學萌起的年份來看,其實這是相當晚近的現象,並不是那麼的理所當然。一般認為近代科學萌起的重要標誌之一,是一六八七年牛頓的發表《自然宇宙的數學原理》,在那個年代中的一六六○年設立的英國皇家學會,也只是一個半民間學社的組織,稍後成立的法國科學院,由於得到法皇的資助,比較可以視為近代科學資助體系的濫觴。
政府支持科學研究當然是以二十世紀最具代表性,其起始關鍵是美國電機工程專家布舒(Vannevar Bush)給羅斯福總統的報告〈科學——無窮的疆界〉。
布舒的報告出於盤尼西林以及二戰時原子彈和雷達發展成功的社會樂觀氛圍,布舒也成功運用了科學的社會行銷,因為他提倡要資助的是純粹研究,但是對於政客與社會大眾來說,「純粹」研究會帶來「實際」應用,似乎難以想像,因此他棄「純粹」而改用了「基礎」,「基礎研究」產生「實際應用」,自是順理成章。
一九五○年,美國開風氣之先,設立了政府資助「基礎研究」的組織「國家科學基金會」,之後許多國家紛紛仿效,歷半個多世紀至今未衰。二十世紀下半葉的冷戰對峙之局中,這個科學資助體系運作功效堪稱成功,原因甚多,嬰兒潮人口大量增長,經濟的快速發展,是客觀大環境的有利因素,延續自上半世紀科學突破的知識發展,也帶來不計其數的技術進步,其中半導體材料電晶體的發明,帶來電腦技術的新時代,最是代表,這個資助科學研究的體系也就水漲船高,日益膨脹,因而引致出許多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