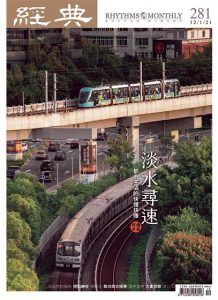從高處往下俯瞰,蒙特內哥羅(Montenegro)首都波德里察(Podgorica),仿若躺在綠色大地上俏皮吐舌頭,從斯庫台(Shkodra)湖入口為起始,一直延續至澤塔(Zeta)河。這塊平原將連綿山峰從中阻隔開來,每年冬天,白雪覆蓋山頂,銀光耀眼,成了巴爾幹(Balkans)半島的地理標誌與精神原貌。從海洋到河口衝積平原,全國唯一鐵軌從沿岸延伸至首都,再一路銜接塞爾維亞(Serbia)。
蒙特內哥羅曾與塞爾維亞合組為一國,直到二○○六年才分道揚鑣。蒙特內哥羅預計於二○二五年加入歐盟,歐盟不僅樂見其成,還投注了兩千萬歐元,以提升蒙特內哥羅的生活素質與振興當地的基礎建設,包括改善鐵路系統的安全與可靠度。
土耳其傾力修復鄂圖曼文化
車站外人潮洶湧,旅客如織,數十台計程車停靠路邊,五顏六色的車頂,搭配九○後的聖痕圖案車身,炫麗而招搖。這一國之都的公共交通系統隨著之前巴爾幹社會主義被揚棄而乏善可陳,計程車成了城內最主要的移動工具。
到首都波德里察走一趟,便會發現這是個不易解讀的城市,國際伯奇(Burch)大學建築系教授厄米納解釋:「這裡不論現代建設或歷史建築都難以理解,比方說,這些都市結構一般不帶任何鄂圖曼文化的元素在內。」鄂圖曼統管當地直到一八七八年,長達五百年期間,僅留下小面積的老社區斯塔拉瓦羅思(Stara Varoš),還有幾個遺跡與紀念碑,鐘樓便是其中一個。十七世紀以石塊建成的鐘樓,保有典型鄂圖曼建築風格,但鐘樓頂端卻被奧匈帝國的密使們裝上十字架,藉此宗教符號宣稱基督徒已重新奪回城市的主權。二○一二年,「土耳其援外總署」(Turkish Agency for Cooperation and Coordination, TIKA)出資將鐘樓修復整頓一番,並在大鐘內重置新的電動機芯。過去十年內,土耳其已斥資一億九千三百萬歐元挹注蒙特內哥羅,這是現任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展現典型「新鄂圖曼主義」的文化外交手段之一;而土耳其國旗的白色新月持續照亮此地,讓巴爾幹半島的其他小國欣羨不已。
建築系教授表示,若沒有土耳其的金援,許多鄂圖曼建築恐怕將被持續埋沒,不見天日。其實,從二○二○年開始,專為推廣首都文化與觀光的「波德里察旅行社」社長艾莉娜(Irena Rogošić),對此早有警覺,而有意識地把這份隱藏的文化瑰寶公諸於世,她坦承:「我們發現這一區是有待發掘的寶藏,過去太少被關注,所以我們規畫了一段從斯塔拉瓦羅思這個鄂圖曼老社區出發的文化歷史路線,其中行程包括土耳其浴、哈茲帕夏(Hadži Paša)橋、鐘樓、斯塔羅多干斯卡(Starodoganjska)清真寺與奧斯曼納吉斯(Osmanagići)清真寺。」波德里察曾歷經二戰轟炸摧殘,歷史遺跡所剩不多,艾莉娜深知這是將文化整合於旅遊的契機。
順著莫拉查河往下,映入眼簾的,是都市中最歷盡滄桑的老城區,飽受中世紀各場戰役摧毀而留下的圍籬、廢墟、階梯,隨處可見。對岸的波德里察飯店,由國內第一位女性建築師拉德維奇(Svetlana Radevic)於一九六七年蓋成。厄米納教授指出,這家飯店是社會主義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建築典範,建築風格融合過去與現在,而且建築元素還舊物回收,將鄂圖曼老社區斯塔拉瓦羅思的廢墟瓦礫都派上用場。這段由建築傳達出歷史和當代之間的對話,令人驚豔,只可惜周遭笨重的玻璃與鋼筋塔樓,遮蔽了飯店的優雅風華。「眼前所見的一切,以最佳的存在方式,詮釋了這座城市的過去與現在。符合現代社會需求的建設既難以避免也無可厚非,但這樣一座突兀的現代化建築,確實欠缺從巴爾幹半島的歷史與天然結構的整體角度來考量,這一點比較遺憾。」
蒙特內哥羅曾在鐵托(Josip Broz Tito)總統近四十年的領導下,成為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一員。對南斯拉夫懷舊的旅人,若一心想尋找鐵多格拉德(Titograd),那這是最佳起始點。鐵多格拉德是首都舊名,同時向昔日國家領導鐵托致敬。這裡最主要的廣場與街道都反映了當年君主制度的光芒華麗,包括彼得一世與尼古拉一世的君王雕像,當然也保存當年軍事時代的遺風跡象,包括紀念亂世期間傷亡的士兵與游擊隊員。或許歷史中的鐵多格拉德城最重要的貢獻,在於保存了首都的設計與建築結構。以當年的時代背景而言,真正的遺跡集中於野獸派的住宅建築風,綠化空間與四通八達的交通脈動。九○年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戰爭,與隨之而來的經濟危機,破壞了公共空間的秩序,原來的完整結構被打得支離破碎,為所謂的「都市化之傾覆」大開方便之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