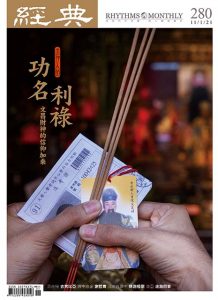西薩.高盧(Cesare Galli)擰開瓶身標示著「Fatu NWR x Suni NWR, 9. 4.21」字樣的液氮罐蓋子,取出樣本,一件稀世珍寶就這麼呈現在我們眼前:一對於義大利北部克雷莫納(Cremona)的阿凡提(Avantea)生物實驗室培養成功的北非白犀牛胚胎。
又稱北部白犀牛、北白犀的北非白犀牛,全世界目前僅存納金(Najin)和法圖(Fatu)兩隻雌性,可說是宣告絕種。所幸在科學家們鍥而不捨的努力下,截至目前,阿凡提實驗室已經成功以人工授精的方式,製造了九個北非白犀牛的胚胎。下一步則是與「拯救生物聯盟」(BioRescue)合作,進行北非白犀牛的復育計畫。
阿凡提生物科技(Avantea bio-tech)是一家從事動物繁殖與復育的公司,創辦人兼總監的高盧,對此次北白犀的復育工程寄予厚望,迫不及待地等候第一隻人工北白犀寶寶的問世。
阿凡提實驗室是第一個採用ICSI技術的實驗室。所謂的ICSI技術,指的就是將單精蟲注射入卵細胞質以產生胚胎。這項人工授精技術除了應用在動物復育計畫之外,也是治療人類不孕症最被廣泛使用的科技。而在生物學上,跟犀牛關係最密切的農畜動物是馬,阿凡提實驗室將馬隻育種的準則,應用到北非白犀牛胚胎的製作。
此前,高盧曾花了許多年,試圖優化蘇門答臘犀與南非白犀牛之間的交配,可惜過程中遭遇失敗,計畫胎死腹中。皇天不負苦心人,終於在二○一八年成功培育出一個南北犀牛的混血胚胎。
從二○一九年以來,陸續成功製造的九枚北白犀胚胎,目前以-196℃冷凍保存在阿凡提實驗室。這些胚胎的精子與卵子,分別取自已死亡的公犀牛蘇尼(Suni),以及現年二十歲的母犀牛法圖。而從法圖三十一歲的媽媽納金身上取得的卵子所進行的人工授精工程,可就沒這麼幸運。在證實失敗後,科學家正考慮銷毀那些受精失敗的卵母細胞。
由於納金和法圖體內都無法執行胚胎著床的任務,科學家決定找其他的南非白犀牛擔任代理孕母一職。
一個物種因某項因素遭逢滅絕後,整個生態系統也將連動性地失衡。犀牛是整個生態系統極具代表性的一環,牠們的生存關鍵全繫在責無旁貸的人類身上。以南非白犀牛為例,先前也跟北非白犀牛一樣,面臨危急存亡之秋。所幸在南非當地團體的竭力保護下,數量一躍來到了兩萬頭之多。
而北非白犀牛就沒有那麼幸運了;由於生存地多處戰火瀰漫之區,如烏干達、查德、蘇丹、中非共和國和剛果民主共和國境內,烽火連天之下連人命都難保,更遑論動物。命運多舛的北非白犀牛,也只能成為人類惡鬥下的無辜犧牲者了。
全球僅存的兩隻北非白犀牛法圖和納金,目前被豢養在有著三層電子圍籬保護著的肯亞奧佩杰塔自然保護區(Ol Pejeta Conservancy)。這對母女似乎並未被本身族群即將滅絕的議題所干擾,依舊安穩地過著自在生活。
每天六點到九點,可以看到法圖和納金沿著大約二.八平方公里的豢養地悠哉地低頭吃草;到了夜晚,母女倆則是在四周布滿荊棘、中央覆蓋舒適溫暖的稻草中安靜休息。一旦天氣變得乾熱,牠們就會補足水分,然後靜靜地躺在樹蔭下休息,等到天氣稍微轉涼些,再繼續外出吃草。遇到下雨天,母女倆就會來個即興泥浴。平日也不忘利用保護區裡的樹木,磨磨頭上的犀牛角。
奧佩杰塔自然保護區的管理員札卡里.穆塔伊(Zachary Mutai)稱這對母女北白犀為「最快樂的農場公務員」。問穆塔伊牠們為何快樂,他回答:「食物是關鍵。成捆的稻草幫助了納金和法圖度過了無數季乾旱,一天兩公斤的紅蘿蔔也提供了充分的營養。」
深悉這對稀有動物特性的穆塔伊,三不五時會摸摸納金的耳後、拍拍牠的側腹,這些安撫動作拉近了彼此距離,也總能讓納金的表情頓時變得柔和安順;而年輕的法圖則不同,深奧莫測的情緒,讓穆塔伊敬而遠之,盡量保持一定的距離。
北白犀的存續
作為世界第二大陸上哺乳動物,納金和法圖若想讓人類斷魂於足下,簡直是輕而易舉。也因此,在一開始照顧這對母女時,穆塔伊抱持著戰戰兢兢的態度,互動時始終是輕聲細語,不敢提高音量以免驚嚇到牠們。對納金和法圖的脾氣瞭若指掌的穆塔伊,過去幾年花在北白犀身上的時間,遠超過和家人相處,也因此熟稔了牠們所有的習性。
「對我來說,納金和法圖就是我的家人。牠們不會說話,也許也聽不懂我所說的話,但我還是經常跟牠們說牠們有多特別,以及我有多愛牠們。」穆塔伊跟我們分享了他與這對稀世動物的相處之道。
穆塔伊既是犀牛專家也是愛好者,即便僅是盯著納金和法圖吃草這個單調的行為,也總能看出一臉興味。像兩台自動割草機般,這對稀有北白犀就在我們前方一邊吃著草、一邊步履悠悠地往前行進。偶爾傳來放屁響聲,穆塔伊也僅是舉起手指,示意我們暫停腳步。幾秒鐘後,沿著前方母女檔的足徑,繼續我們的邊行邊聊。
納金和法圖出生在捷克的德武爾克拉洛維動物園(Safari Park Dvůr Králové),目前該野生動物園仍是這對母女北白犀的合法擁有者。納金的父親、法圖的外公就是當年全球僅剩一頭的雄性北白犀蘇丹(Sudan)。
二○○九年,這對母女犀牛和一頭名為蘇尼的公犀牛被轉送到肯亞的奧佩杰塔自然保護區,保育人士希望這裡的環境能幫助牠們重拾對生活的熱情,順利繁衍下一代,為北非白犀牛的存續打開一線生機。
然而復育計畫進行得並不順利,交配結果宣告失敗。二○一四年,蘇尼壽終正寢,享年三十四歲。全球最後一隻雄性北白犀蘇丹,也在四年後宣告死亡。
蘇尼的死亡,讓整個奧佩杰塔自然保護區的工作人員哭紅了雙眼。「蘇尼是我們所有人的朋友,我有幸在牠生命的最後一刻,陪伴在牠身旁。」穆塔伊跟我們說道。
二○一五年,捷克獸醫團隊證實納金和法圖已無法自然繁殖下一代。納金由於過去經年累月被關在牢籠,以至於後腿萎縮無法承受公犀牛的體重,再加上去年十二月發現靠近左卵巢的胃部長有腫瘤;女兒法圖的子宮則被診斷出有病理性的退化。所幸健康狀況仍屬良好。
來自五大洲二十名科學家組成的專案小組制定了北非白犀牛的救援計畫。科學家考慮以幹細胞技術進行此項計畫,然而除了技術本身的複雜度與費用昂貴,母犀牛的生理構造問題:不超過人類拳頭大小的卵巢,也讓取得卵母細胞成為一項極具挑戰性的工作。
犀牛是地表第二大動物,想從其身上取得卵母細胞,難度著實不易克服,需靠大量鎮靜劑的注射方得以完成。此外,整個幹細胞技術進行的過程中,道德風險評估也需納入考量。
「經過全面審慎評估,我們確定了這項卵母細胞擷取行為,並不會傷害到母犀牛的身心健康。」奧佩杰塔自然保護區首席獸醫史蒂芬.恩格魯(Stephen Ngulu)表示。
擔任此次代理孕母的四頭母南非白犀牛,過去已有充分的代孕經驗。在胚胎植入之前,牠們被安排事先入住奧佩杰塔自然保護區內,以便科學家對其生殖週期進行更深入的研究。
科學家打算先將一個南非白犀牛胚胎植入母體,如果母體成功接受,接著再植入北非白犀牛的胚胎。新冠肺炎疫情的大爆發,使該項復育計畫暫時中斷,但奧佩杰塔自然保護區內的工作人員堅信這項計畫將能在今年完成。計畫若成功,這將是全球首例對犀牛進行人工授精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