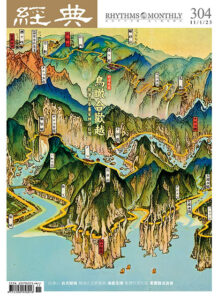在愛爾蘭的荒野上,生活著一群真正的游牧民族,他們被稱作流浪者(Lucht Siúll,或稱Minceir,意即「行走的人」),也有人喚他們修理匠(Pavee)或旅行者(Travellers)。普羅大眾經常將他們與吉普賽人(Gypsies)、羅姆人(Roma)或辛提人(Sinti)搞混,但他們之間並無血緣關係。即使與前述幾個游牧民族一樣,面臨文化與傳統流失的問題,但流浪者是官方承認的獨立民族,與愛爾蘭當地的定居民族有所區別。
流浪者的人口現約有兩萬五千人,僅占愛爾蘭總人口的1%,不過根據民間傳說,他們是愛爾蘭最早的住民,甚至比我們熟悉的凱爾特人(Celts)要來得更早,而不僅愛爾蘭,在英格蘭、威爾斯,甚至北美洲都能看到流浪者們的身影。
流浪者主要使用雪爾塔語(Shelta,又稱Cant或Gammon),它是一種混合拉丁語系、英語,以及愛爾蘭語的方言,擁有悠長的歷史。然而就像大多數的傳統語言一樣,它以口述為主,缺乏文字的記載,因此若想深入了解他們的文化,得實際拜訪,與他們交談,親耳聽聽他們的歌謠和故事。
以家族羈絆為榮的浪子
流浪者每年的最大盛事,就是一年二度的馬匹販賣會,分別是六月以及十月,在英國阿普比(Appleby)以及愛爾蘭巴利納斯洛(Ballinasloe)舉辦,全國的流浪者們將在此齊聚一堂,聯絡感情之餘,展示並交易他們悉心飼育的美麗馬匹,馬匹的鬃毛被梳理得蓬鬆飄逸,奔跑起來更顯翩翩瀟灑,此一傳統自古傳承至今,流浪者們引以為傲。
但他們自豪的傳統,也無可厚非地招致了批評與歧視,他們被稱作「屠馬者」(Knackers),或是「賣馬屍體的人」。但流浪者出身的影視界人物們,例如演員兼編劇的約翰.康納斯(John Connors),不僅不在意這些負面形象,甚至還借力使力,據此創作出富含魅力的作品。膾炙人口的英國電視劇《浴血黑幫》(Peaky Blinders)就是由真實故事改編,描述十九世紀時英國伯明罕一個黑幫家族的故事,他們將刀片縫進帽沿作為暗器,以偷襲聞名,而鮮為人知的是,劇中的土匪強盜們的形象,便是以流浪者為原型所創造出來的。
關於流浪者的起源,還有另一個傳說,據說他們的祖先是一位錫匠,在耶穌被釘於十字架上時,所使用的釘子因為是由這位錫匠所鑄造的,他的後代因而被判永世游牧,不得定居之刑。祖先的罪業,卻由後世代代承受,這個傳說如今聽來雖有些荒誕,但流浪者似乎並不認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一種刑罰或詛咒,他們十分熱愛,並以這樣的生活方式為傲。
與歐洲其他民族相比,流浪者們的平均年齡較為年輕,根據習俗,男性在二十歲前後便會娶妻,女性的出嫁年齡則更早,落在十七歲左右。流浪者的生育率相當高,一個家庭有十人以上的成員都不足為奇,今日,即使他們也不免俗地受全球晚婚、少子化的浪潮所影響,但悠長歷史中所堅守的,建立牢不可破的家庭關係,這樣的傳統價值觀仍舊不變。男女平權的概念,則是流浪者社會中的另一個核心價值,我注意到在一個群體的領導者中,通常都會包含一名女性。
說到流浪者們的信仰,大多數的流浪者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而彷彿為了彌補先祖在古老傳說中的罪過一般,鑄造釘子仍是他們的傳統習俗,他們遵循傳統羅馬天主教的儀式與教義。然而對傳統習俗的堅信,讓他們在面對疾病時,更傾向祈禱而非醫療行為,至於治癒效果那就見仁見智了。
雖然崇尚自由,但家庭間的羈絆仍是流浪者社會的核心價值,從他們對婚喪喜慶,以及前述年度盛會的重視中,我們能看出「齊聚一堂」對流浪者們別具意義,也正因為這些交流與相處,以口述為主的文化傳統才得以保留下來,流浪者們方能在這瞬息萬變的社會中,將自己的根本銘刻在心。
流浪者的傳統篷車稱作「瓦多」(vardo),它以精美的裝飾、複雜的雕刻、明亮的彩繪,表現出每位流浪者與其家族的個人特色。身分地位較高的流浪者,往往擁有更精緻華麗,甚至鍍金的瓦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