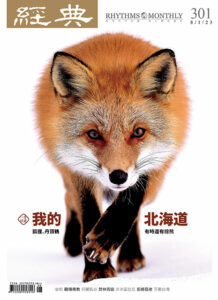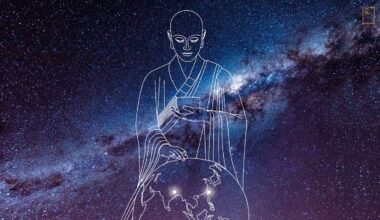討論藏傳佛教史,不妨從這個信仰如何被認識著手。
台灣人對藏傳佛教開始有所耳聞,約在資訊稀缺的一九七○年代;而其認知多止於金庸筆下「西域來的番僧各個身懷絕技、武功高強」而已。例如《天龍八部》,背景設定在北宋哲宗年間,裡頭有個出身大雪山大輪寺、外號「大輪明王」的鳩摩智。他貴為吐蕃國師,天資聰穎,嗜武成癡,是武功絕頂的高手,雖滿口佛理,卻行事陰險,不擇手段,也無寡慾與慈悲之心。
另一部時間跨度在南宋寧宗到理宗時期的《射鵰英雄傳》,也有個青海手印宗(原版為西藏密宗)高手靈智上人,以武功「大手印」、五指祕刀與毒砂掌馳名西南,是個心智、武功俱毒辣,晚景淒涼的大喇嘛。而時空背景接續為南宋理宗年間的《神鵰俠侶》,精研密宗護教神功「龍象般若功」,成就空前第十層境界的蒙古國大法師金輪法王。他雖出身佛門、身披黃袍,卻有別於出家人慈悲為懷的形象,是個背信忘義的卑鄙小人,也是中原人士所不齒的奸僧。
與番僧相對的漢地僧人,則以少林寺為代表。由於佛教有超越地域、國界的特點,金庸常以少林寺作為諸小說中綰合情節、提調線索、領袖群倫之樞紐;即使少林寺驟臨群雄圍攻,也自有隱居的高僧化解孽障。對比之下,金庸筆下來自蒙古、西藏、青海的番僧、胡僧,則是神祕的外來門派,出人意表、變幻莫測。這固然是小說書寫中呈現正反張力的手法,然喇嘛的人設,全係頂級的反派角色,俱為江湖上大奸大惡之徒,其立場、理念皆與中原文化相悖。讀者們也多因虛構的小說情節,對藏傳佛教人物留下負面、甚至錯誤的印象。
奇幻故事的香格里拉憧憬
繼金庸武俠小說之後,來自西方的翻譯書再度掀起藏傳佛教熱潮。這次的時間背景是當代,而藏傳佛教也從故事的反派配角,一躍成為奇幻故事主角,主要受眾也從普羅大眾轉為佛教信徒。
一九七九年,台北天華出版社發行了羅桑倫巴(Lobsang Rampa)的《第三隻眼》(The Third Eye),此後更有《生命不死》、《藏紅色的法衣》等七本中譯圖書連續問世。作者以第一人稱的方式,說自己出身西藏十大貴族,自幼被達賴喇嘛選入寺院進修,又在額上進行了頭骨手術,植入了水晶石英片,開啟天眼通、他心通及神游等能力云云,再一次帶動了東西方對藏傳佛教的關注。
該書作者原名瑟瑞爾.亨利.哈斯金(Cyril Henry Hoskin)。他以西藏人名義撰寫出版的英文自傳書籍達二十餘本,自一九五六年起在倫敦陸續出版且十分暢銷。但著名的西藏探險家海因里希.哈勒(Heinrich Harrer)並不相信那些書的內容,於是聘請私人偵探,調查出羅桑倫巴是出生於英國鄉村的水管工之子,高中輟學,既不會藏文也從未到過西藏。書中描述在西藏成長、修學佛法及海外流亡的經歷,都是用圖書館裡收集的西藏與佛教資料編成,純屬虛構故事。
有趣的是,作者被揭發後仍繼續利用當時的熱潮巧妙進行辯護,宣稱羅桑倫巴確有其人,但英年早逝,是以靈魂轉移的方式占據他的身體。由於他的作品與某些「新時代」(New Age)思惟相通,持續吸引眾多信徒,成為新時代思潮的引領與宣揚者之一。
羅桑倫巴著作所傳達的雖非正確的佛教或西藏佛教教義,但歐洲有不少藏學家和佛教學家,都是因為著迷於《第三隻眼》等書所描述的西藏文化,才走上專業學者的道路。連第十四世達賴喇嘛都說:「雖然這些書是虛構的,但它們為西藏做了良好的宣傳。」
烽火連綿下的契機與底蘊
除了武俠小說與奇幻故事所虛構的藏傳佛教之外,一九四九年前後其實有內蒙古的第七世章嘉與第五世甘珠爾瓦兩位高僧,在大時代的變動中先後隨國民政府來台。他們以邊政需要為由,位居漢傳佛教會要職,可惜當時因缺乏翻譯人員與經書法本,並不具備弘揚蒙藏佛教法義的成熟機緣。
一九五九年,因局勢所迫,大批藏僧、藏人離鄉背井,流亡印度。由於路途險阻,劇烈的氣候與飲食差異,初期的艱困難民生活,令許多人喪失了寶貴的生命。在西藏千年佛法文明風雨飄搖之際,善業種子從不令人失望。在佛法故土印度的西藏難民們,歷經前十年的奮鬥求生,基本生活稍得溫飽後,便全力投入修建寺院、護持僧團,並進一步興辦佛學院教育,延續關房的實修傳統。新一代的年輕上師,在印度得到學習英語的機會與環境,自一九七○年代起陸續前往歐美弘法,從而開啟全世界的佛法新篇章。一九八○年代台灣經濟起飛,社會大眾對精神提升的渴望,吸引著藏傳佛教的弘法先驅來到寶島,台灣的佛子終於有了直接面對面接觸藏傳佛教傳法上師的契機。
究竟誰是一九八○年代第一位來台的藏傳佛教僧侶,至今莫衷一是;但一九八二年第一世卡盧仁波切首度來台弘法,無疑是藏傳佛教在台灣的第一個輝煌。卡盧仁波切曾閉關實修數十年,在一九七一年成為第一個到歐洲、北美等西方國家傳法的西藏上師。首訪台灣時,在電視明星陳麗麗等人的協助下舉辦法會,又與南投水里蓮因寺懺雲法師交流,受到法師推崇,化解了部分漢傳學佛者對密宗的成見,也展開了台灣藏傳佛教的新頁。
由於台灣的經濟實力與信眾的樂善好施,在供養、護法與傳法的互動下,來台的藏傳佛教僧侶數遽增,最高時每年近兩千人次。這次佛法經空中航線從印度到歐美,再輾轉傳入寶島。是以初期台灣的藏傳佛法,主要藉英語弘傳;時間上雖晚歐美十年,卻使得已經西化的台灣新世代,能夠透過淺白的英語,更容易吸收佛法的精華。在漢傳佛教的原本信眾之外,意外開拓出新的、更年輕的信仰群。這次不再藉由虛構的武俠與奇幻小說認識藏傳佛法,而能在傳承千年佛教的西藏傳人面前,聆聽口耳相傳的佛法詮釋,學習彼等仍代代實踐的禪修技巧。關於西藏與藏傳佛教的真實輪廓,也在多年的傳習中漸趨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