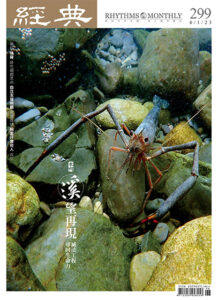少年們的肩上扛著沉甸甸的卡拉什尼科夫步槍(Kalashnikov),胸前的口袋則插著梳子,一頭烏黑長髮下的雙瞳骨碌碌地轉動,閃爍著危險的光芒,他們上下打量著等待通關的人們,再低頭慢悠悠地佯裝閱讀著手上的各項文件,直至接獲一通來自上級的電話後,緊張的氣氛才得以緩解,少年兵們放下戒心,甚至開心地和驚魂甫定的記者們合照,此時的他們,看起來才像是這個年紀的孩子。
這些目光如炬的武裝少年就是阿富汗的新主人:塔利班的新成員。這個惡名昭彰的組織近年來致力於走年輕化路線,年輕人試著讓自己看起來像一支真正的軍隊,他們眼神無懼,卻仍可見幾分稚氣。方才的提防與下馬威其實有遠因的,畢竟阿富汗正從多年的戰火中解放;自古以來,從日不落的大英帝國,到軍事強國俄羅斯,外族對阿富汗的威脅從沒少過。
阿富汗的新主人 年輕少主
年輕人加入塔利班的原因有很多,但比起宗教狂熱,更多是為了免於挨餓。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與世界糧食計畫署(World Food Programme)的統計,在美軍撤離後的今天,阿富汗失業率高達98%,超過兩千四百萬人亟需人道救援,即使身為少數的受薪階級,薪水遭積欠數個月也是家常便飯。
「我身為塔利班,對信仰無庸置疑,但艱苦的生活幾乎已讓我對我們所信奉的神失去了信心。」一位年輕人受訪時如此說道。
阿富汗位於亞洲的中心,同時也是東西方世界交會點,這裡不僅是兵家必爭之地,更是無數牧民、商旅進出亞洲的門戶。作為世界上最適合游牧的地點,即使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仍有許多人遵循著古老的傳統,領著牛羊群穿梭於群山之間。我們這趟旅程的目的,便是探索在俄羅斯入侵後的這四十年間,游牧民族的生活出現了多少變化。
我們選擇庫奇(Kuchi)人作為研究對象,庫奇人是普什圖(Pashtun)人的一支,自古以來便在巴基斯坦與阿富汗之間遷徙。然而,找尋一個游牧民族並非易事,我們只能依據當地居民提供的模糊線索,跋涉數百公里,在一座座牧場間來回奔走,終於,在阿富汗東部的拉曼(Lahman)省,喀布爾河的源頭,我們見著了庫奇人的廬山真面目。
在阿富汗漫長的歷史中,經歷了無數的戰爭與侵略,但似乎都與這片清新如翡翠般的牧場無關。這裡宛如世外桃源,遠離戰火,當我們遠遠看見庫奇人的帳篷與他們的羊群時,我們興奮不已,加快腳步;在跋涉過一條水深及腰的溪流後,我們遇見了牧民達萊(Dawlai)。目光銳利的他散發出一股渾然天成的自傲氣質,從周圍的牧羊人都叫他「指揮官」的態勢來看,達萊顯然就是這群牧羊人的領袖——至少在這趟從喀布爾出發的旅程是如此。
「我們每年都帶著羊群前來,但近年卻開始與土地的新主人發生衝突。」我們啜飲著綠茶時,達萊說道。「他們想把這裡變成農地,因此開始驅趕我們,甚至用無人機來追趕我們的羊,牠們嚇壞了,我們只能把牠們趕進帳篷裡躲避。」一旁的老牧羊人義憤填膺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