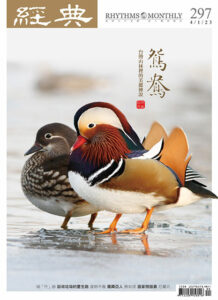埃及首都開羅(Cairo)與地中海間那片肥沃的三角洲,僅占埃及3%的國土面積,卻居住了近四千萬的稠密人口,且扛下全國12%的GDP,以及兩成的勞動力,數千年來,尼羅河三角洲擔當埃及經濟命脈與糧倉的角色,同時也是歐非大陸間的戰略要地。從上空鳥瞰埃及,在一片漫漫黃沙之中,鬱鬱蔥蔥的三角洲十分搶眼,埃及的傳統標誌——生命之符安卡(Ankh),其前端水滴狀的圖案,就是以這片象徵生命的三角洲為原型。
在古埃及文中,有兩個詞代表土:「Kemet」與「Deshret」,前者指沙漠中乾燥的紅土,後者則指三角洲肥沃溼潤的黑土。自古以來,在埃及人眼中,土只分為兩種:來自三角洲的土,以及三角洲以外的土,這足以證明尼羅河三角洲的特殊地位。這裡不僅孕育了古埃及文明,更從法老與金字塔的年代前,就是羅馬帝國重要的糧食產地。然而,在數千年後的今天,這裡即將面臨艱鉅的挑戰。
埃及的人口在四十年內,從四千五百萬暴增為一億多人,土地的負荷與古埃及時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三角洲能夠負荷爆炸性成長的人口嗎?而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水資源的短缺等種種問題,更是雪上加霜。
拿破崙曾如此評論埃及:「若管理得當,尼羅河能戰勝沙漠,反之亦然。」埃及人秉持人定勝天的精神,建造了亞斯文水壩(Aswan Dam),讓尼羅河例行的氾濫,不再威脅沿岸居民與農田的安全,更使農地能夠一年種植三種作物,最大化發揮糧倉的功能,但也並非百利而無一害。
水壩擋下了來自上游的沉積物,造成海岸嚴重侵蝕,加上海平面上升所造成的海水倒灌,近15%的肥沃農田毀於一旦;而由於來自上游的養分被擋下,使得農夫們必須大量使用化肥以維持土壤的肥沃度,化肥造成的鹽度上升與化學汙染,影響了居民的飲用水安全,漁業的發展也因此飽受威脅。科學家試圖以研發更強韌的植物品種等方式力挽狂瀾,但效果也有限。
逆境中的信仰支柱
世世代代耕作於運河沿岸的法拉欣人(Fellah)即使無奈,也只能逆來順受。他們的處境,仍如埃及知名作家陶菲格.哈基姆(Tawfiq al-Hakîm)一九三七年的著作《鄉村檢察官的日記》(Diary of a Country Prosecutor)所描述的那樣,既貧困又落後。
「童年的味道跟故鄉的景象,是我不願回首的回憶,我已經受夠了。」馬哈茂德(Mahmoud)嘆道,他畢業於歷史與考古學系,如今在開羅工作。「或許等我退休後,我會選擇回鄉務農,但現在我仍會想盡辦法留在開羅發展,城市有更多工作機會與資源,至少生病時有醫院可看病,若有小孩也有學校可上學。」遵循傳統生活的農民們,跟不上現代化的腳步,耕地漸漸被改建成高樓大廈,價格也漸漸高攀不起,即使沒日沒夜地辛勤耕作,仍然被債務與通膨追得喘不過氣,農民自殺率節節高升,對他們而言,只有移民到首都,才能找到翻轉命運的契機。
日子不好過,信仰作為人們的精神支柱更顯得重要。位於開羅北部的坦塔(Tanta),是埃及穆斯林的朝聖勝地,當地的清真寺紀念著名的蘇菲派聖人艾哈邁德.巴達維(Sufi Syyed Ahmed al-Badhawi)。「他除了是穆罕默德家族的一員,還是一名有名的學者!」希赫克(Sheihk Ragab Ramadan)向我說明「就算來到電視與電腦的時代,不變的是,生活始終是生活,家庭始終是家庭。」他用這段富含哲學意味的話總結。
穆斯林們朝聖古老的聖塔達米那教堂(Coptic church of Santa Damiana),基督徒們則參加伊斯蘭的宗教儀式,在坦塔,沒有宗教間的劍拔弩張,只有對彼此虔誠信仰的尊敬。每逢朝聖時節,信徒們不分男女老少,無懼熾熱的高溫,一車一車地前來。「基督徒與穆斯林參訪彼此的聖地,你能想像嗎?傳統信仰與現代地球村的概念在此交融,呈現出其他地方看不到的景象。」伯特斯(Botros)神父看著這副光景,既感慨又帶幾分自豪地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