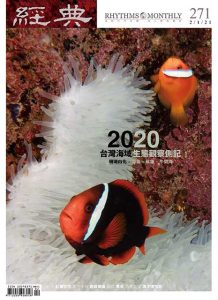若非那輕到不易察覺的金屬摩擦聲,恐怕所有乘客都渾然不覺這列火車已從奧斯陸(Oslo)出發,準備前進歐洲最險峻而迷人之地。
歐洲大陸最高與最重要的卑爾根(Bergensbanen)鐵道,穿越挪威東西兩岸的高山——一邊是挪威東部的峽灣與崇山峻嶺,另一邊則是挪威西部的大西洋海濱,將首都奧斯陸與挪威第二大城卑爾根(Bergen)連結起來。大雪紛飛的嚴冬時分,除了一路美不勝收的壯闊景致令人驚歎,這趟歷時七小時的鐵道之旅,如詩如畫的背後,是長達四百九十三公里的鐵軌、三百座橋梁以及一百八十二座總計七十三公里的隧道。
旅途之始,火車安靜地悠遊於鄉鎮之間,眼前的迷人小城,仿若從雪白地毯冒出來般,每一瞥都像畫,車廂內的乘客紛紛舉起手機,雙眼緊盯著手機螢幕為他們定格的美景。過去,搭乘所謂的浪漫鐵道旅程,必須忍受一種近乎空無且遺世獨立的孤寂,偶爾從窗外隱然可見大都會與文化之都所傳遞的溫暖與光芒,但也總是稍縱即逝;但現在,當火車緩緩穿越歐洲最高的哈當厄爾(Harangervidda)高原時,相較於過去在極端荒野行駛的冷寂,現在的乘客可以在溫暖的車廂內,欣賞從北極圈吹來的漫天風雪,與目不暇給的壯麗山河。
蓋一道連結奧斯陸與卑爾根之間的鐵道,這樣一個充滿遠見的大工程,其實是沃斯(Voss)林務局局長格羅森長久以來的夢想。一八七一年時,只有船隻航行於連結兩座城市之間的斯卡格拉克(Skagerrak)海峽;而被層巒山峰阻隔兩地的奧斯陸與卑爾根,城市性情迥然不同,東岸天候宜人,西岸則酷寒難當。蓋鐵道的提議,可想而知,幾乎立即引發憤怒民眾的抗議。許多人甚至預言,誰斗膽侵犯群山的神聖,必遭來可怕的天譴。也有人憂心這些開發工程必然破壞大自然的地貌與山河,這些恩賜的國本,都是不久前才獨立的挪威小國最引以為傲的國家認同。
人定勝天之大考驗
儘管北歐民族的硬漢性格很難搞,爭議不斷,困難重重,但挪威仍號召近兩千名來自鄰國瑞典的工人,蓋起了一座約一百公里長的鐵道,在高於海平面六十公尺之處,蜿蜿蜒蜒地從卑爾根的峽灣,接到沃斯。但距離理想中的鐵道,還差七十五公里,而且最棘手的難題——要在制高點搭起鐵軌,需要爬上海拔一千兩百五十公尺高的山峰,尚未有解套。一開始,工程總經理找來義大利籍工程師,想藉助他們在阿爾卑斯山蓋鐵軌的經驗,期待他山之石可以攻錯;但挪威的花崗岩山脈顯然不好惹,就連這群有經驗的專家也束手無策,自家問題,終究還是得靠自己來解決。
萬丈高「軌」平地起,他們開始鋪路,運送工程所需的材料到高山,險峻地形外加極端氣候,最普遍的做法是,以馬代勞。除了汗馬功勞,卑爾根鐵道的開通也用了總計超過七百噸炸藥來開通,但仍有許多片麻岩石的隧道,還得動用一萬五千名工人來挖掘。一九○七年,從奧斯陸前進的工人與另一邊從卑爾根開始「步步為營」的工人,東西兩邊終於在侯加斯特爾(Haugastol)相會,但大自然似乎想給人們上一堂「成事在天」的功課,狠狠下了一場災難性的暴風雪,癱瘓工程進度超過一個月。
一九○八年六月十日,鐵軌終於完工,火車順利從奧斯陸出發,挪威第一任國王哈康七世(Haakon VII)親臨終點站卑爾根,歡迎這列具有歷史指標性的火車首航正式啟動。從這一年開始,卑爾根鐵道納入交通的運輸系統,但這列火車仍需持續面對比大岩石更難對付的「天敵」:每一年長達九個月的連綿風雪,尤其行經那段被喻為「挪威屋脊」、數百公里長的哈當厄爾高原時,鐵軌穿越之地,是沒有植被、白茫茫一片荒蕪雪地。
二○○九年,挪威為了慶祝卑爾根鐵道一百週年,拍攝了一部跟著火車慢走、逾七小時的紀錄片,大夥兒對此高度指標意義的國寶級鐵道,津津樂道,難掩驕傲。如果說有任何美中不足,套句車廂吧枱區女服務員說的話:「我們在最貧窮匱乏的時候蓋這個世界級的鐵軌,現在有能力了,卻無法把這條鐵道整修得比較現代化。」
挪威最古老的滑雪場蓋羅(Geilo),受惠於鐵路而讓許多滑雪愛好者可以千里趕來。但一般而言,卑爾根鐵道還是以銜接城鎮之間的交通運輸為主,尤其當極端氣象癱瘓了陸路與航空交通時,鐵道便能取而代之。侯加斯特爾站之後,便是鐵道盡頭,火車準備前進風雪交加的蒼茫之中。
「我們現在看到的,和一般的火車沒什麼兩樣,新的列車已經取代過去風光舊時代的車廂,但我們還是在一些隧道裡保留了一些足夠應付緊急時刻的列車,」一名當地鐵道員再三保證。「新舊的唯一差別在於,新火車處理掃除霜雪的功能,不及舊款的列車強;所以我們得使用一個大型的掃雪機,每一天都要清掃鐵軌上的積雪。」話鋒一轉,他開始解嘲:「不過,坦白說,奧斯陸那邊的同事惹出來的問題,恐怕比冰雪造成延誤的問題更難搞,他們老是搞不清楚那些電子訊號。另外,在二○三○年至二○六○年間,我們這裡還有一個新的高速鐵路工程在規畫中,但慶幸的是,政府沒有採納許多政治人物的要求關閉這條鐵道。他們覺得卑爾根鐵道的維護太昂貴,所以要以高速公路與公車線道來取代,幸好他們最終能夠理解,這樣的規畫會造成生態惡夢。」
彷彿從雪霧中悠然出現的火車,是這個被冰雪籠罩的小鎮與外界連結的唯一管道,曾幾何時,這個一到冬天便與世隔絕的地方,過去只能靠滑雪或機動雪橇才到得了。但大部分挪威人卻視此為無拘無束的自由天堂,人人都可以躲在獨棟小屋裡,享受與世無爭的歲月靜好;儘管有些人家甚至連電力與熱水等基礎設備都沒有,但這便是挪威靈魂與眾不同的精髓,外人難以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