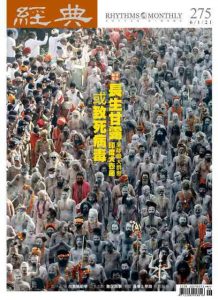金陽和煦,一期稻作緊鄰著結實纍纍的葡萄藤架,綠色稻浪迎風翻飛,本該一幅如畫的鄉村風景,孰知隨著涼風吹來的竟是陣陣惡臭。
如果不是此刻站在鄉間,親眼見到溝圳旁堆積的乾枯葡萄藤摻雜著發出異味的塑膠垃圾,實在很難想像甜美果實的生產現場,背後竟有如此不堪的畫面。
一位阿嬤騎著摩托車緩緩停下來,一陣寒暄之後,才知道原來正是這葡萄園的主人,她也不避諱地告訴我們,堆在水溝旁綁成一捆一捆的葡萄藤是她的傑作,因為實在無處消化,只好先堆著,然後趁某個月黑風高的夜晚,再偷偷地丟進溝裡燒掉。有時候會遭鄰居舉報,引來彼此的不快,但這樣的鄉間衝突與無奈,實在是因為這些農業剩廢無地「去化」。
我想起甫行經的鹽埔交流道旁,一堆看起來不太悅目的物質:葡萄藤、廢木材、肥料袋、農藥罐、敲碎的米酒瓶……,舊時燒過、新近堆積的灰燼上,意外冒生出的芭蕉樹則成了絕佳的遮蔽視角。這是村莊邊界無人聞問的角落,也成了農業剩廢傾倒的絕佳場地。
這些不被注意的「小」問題,都是鄉村的難言之隱。
炭化回歸有機農田
當我四處探問著「農廢」問題時,時常會被糾正:「愛注意喔,請不要說農『廢』,要說農『剩』!」原來大家都很忌諱被說成是廢物。
只要有生產,一定會有剩廢。除了各種果樹修剪下來的枝條,稻米生產所遺下的稻殼、稻稈稻草、木竹下腳料,香菇與花卉的栽培過程中,各種農林剩廢數量其實大得驚人。
葡萄藤既不是家庭廢棄物,也不真屬於事業廢棄物,妾身未明之下,清潔大隊不願收,焚化爐也不給燒,到底何處才是它的歸屬呢?
六○年代,彰化的巨峰葡萄採收後剩下來的葡萄藤枝,農民唯有放一把火燒掉或就地掩埋。六十五歲的賴茂勝是一個熱情的發明家,自嘲自己學歷不高,因此是「博土」;他研究發明出一套「限氧燜燒炭化」技術,將農業後端的剩餘物資做循環運用。
他帶我們來到設置在社區的有機垃圾處理場,向我們展示簡易炭化爐的操作,安全燜燒八個小時之後,炭化的物質可以變身土壤改良劑,改善受農藥長期澆灌後的酸性土壤;蒸餾出的液體冷凝後集成木(葡)醋液,可製成無毒的自然農藥。
三十年前賴茂勝就開始推廣有機農業,讓台灣土地完全不用農藥是他的終極目標,初期希望起碼能達到農藥減半,「農友的環保概念,要透過炭化來建立!」
葡萄農吳英坤、黃雪靜夫婦是賴茂勝在社大授課的學生,跟著他學習如何以簡易炭化爐去化田間雜草及廢枝條,再以生物炭當成果園的肥料,循環利用。過去用堆肥的方式,耗時且效果不佳,「你以為把不要的稻稈、蔗渣堆置到農田旁邊就可以變成天然的堆肥?這其實是人類一廂情願的美夢,實際狀況是,堆放久了會發生惡臭,也不見得真的能達到補充肥分的效用。」
為了防止空氣汙染,政府禁止燃燒農業剩餘廢料,但又未提供妥善的處理方法,一張罰單五千元,被逮到露天燃燒的農民,除了自嘆運氣不好,也只能無奈地欲哭無淚。
大村鄉有五百公頃的葡萄種植面積,一年兩個收成季,連帶產生兩百五十噸的廢棄葡萄藤,一直都是這個葡萄原鄉的一大困擾。賴茂勝說,以他一己之力目前也只能協助去化一百噸的量。他認為處理農林剩廢應以社區為推動單位,「就像慈濟有資源回收站一樣!」從源頭、在地、就近優先處理,善用這些剩廢資材,是實踐循環農業的最佳典範。
農林剩廢的循環經濟
田間的農林廢料數量出人意料之外的多,卻時常受人忽略,然而一年二至四個產季,源源不絕的出現,若未能妥善去化,也將成為產業的困境,讓業者無法安心前端的生產。
農委會估計,台灣農業每年產出約500萬公噸的農業剩餘資源(各主管單位認定、統計的項目及數量,有極大差異),主要可分成三類~
(1)農業生產未利用殘體:包括作物(含林業)生產未食用部分,以及動物毛皮、鱗片及骨頭等。(2)生產過程使用之剩餘資材:包括生物性資產如菇包、水苔等栽培介質、飼料及支架等;非生物性資材包括農地膜、栽培盆、人造介質及固定支架(夾、繩)等。(3)畜禽動物排泄物:養殖動物進食後未能吸收之消化殘餘物。
農林植物剩廢的利用主要有兩個方向:1.炭化,2.能源化。
炭化的碳品除了可以製成肥料,再次回歸農田,也可製成生物炭或有其他更高值化的利用;能源化的部分則可製成燃料棒,作為發電、熱能使用,回到農村提供農產品加工或偏鄉電力供應,也可與台電併聯出售農林生質電能。從農田來的,再回歸到農田去,完成農業的循環經濟。
農林剩廢歸誰管?
來到台中新社,這個台灣香菇養殖的大本營,田間處處可見香菇栽培的設施溫室,蔬食的健康風潮及信仰飲食習慣,使得香菇的培養技術與生產量近年來突飛猛進,產值高達上億,國人一年消費五億包的香菇太空包,其中兩億包來自這裡。
然而,每年產季過後,新社的大名不時會現身各大新聞媒體:「廢棄的香菇太空包被任意傾倒在溪谷大排,造成水源汙染的環境問題。」除了菇農違法,甚至也有不肖的廢棄物處理業者,收了錢,卻隨處堆放不做處置。
曾經是菇農的陳進耘表示,「每年生產香菇之後所產生的一次性廢棄菇包,如果沒有妥善處理,又怎能安心繼續下一季的種植呢?」他在七年前成立了廢棄菇包處理廠,目前的產能已經可以去化新社地區五成以上的菇包剩廢。
跟著他進入鐵皮搭蓋的處理廠,眼前一堆堆彷如廢土的粉塵小山,就是已經以機器將塑膠袋包分離後的木屑,經過粉碎、篩選、烘乾、曝晒、堆置之後,才能被繼續再利用。「你看那種顏色比較黑的,來自香菇包,比較淺的則是種杏鮑菇的培養基。」苦心專研多年,目前的烘乾技術已經能夠客製化地將水分從80% 降至40%、20%,做各種不同的應用,例如製成培養土的介質、肥料,或者壓製成木質燃料顆粒,主要是「肥料化」或「燃料化」兩大用途。
夫妻兩人在進入處理香菇農廢的路上其實備嘗艱辛,三、四年前有一度快要做不不下去。太太吳淑卿表示,設備、技術、資金這一塊陸續到位,都還算好解決,最大的難題在如何克服社會惡感以及農地的合法性問題。
農廢處理廠基本上是個鄰避處所,鄰居的檢舉投訴不斷,「天天被抄」是夫妻倆最大的噩夢。因為堆積的菇包容易發熱,木屑裡面殘留的菌絲會發酵產生異味,因此常常引起鄰居抗議。「但有時候還沒有堆置,就已經有人陳情了。」民眾對廢棄物處理,刻板印象上始終不佳。
此外,因為不懂法規(正確說來應該是法規的模糊)與權責單位的歸屬不明,讓她花了七年的時間在公部門之間來回奔走。「屬於廢棄物再生能源以及栽培介質之原料要跑環保局,農地的合法使用問題,需向地方政府申請農業用地附設農業處理設施,一關一關地闖。」去年十月終於陸續取得各種合法營業的許可文件。
「在田裡歸農委會,剩廢運出農地歸經濟部,如果發電則歸能源局嗎?農業循環再生計畫,到底又歸誰的業務呢?」這是許多農民與廢棄物處理業者的普遍困惑。
因為沒有清楚的政策、找不到跨部門的整合平台,有時候一個人說一套,讓跑單的農民莫衷一是。對於今日人口老化的農村、缺乏知識與資源的農民來說,想要盡力推動農林剩廢的再利用,恐怕是難上加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