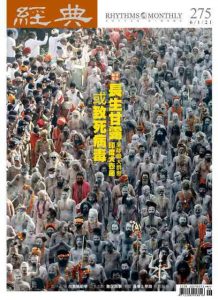正午時分,陽光也無法照射進這峽谷,我們走在峽谷的陰影中,結冰的河面展示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但也考驗著我們維持平衡的技巧。有時上層的冰層融化,留下一面冰水。而當冰層融化的時候,上方的冰層便極易因為我們的腳步而碎裂,在迴音與積雪所悶出的寂靜中,碎裂所製造出來的聲音格外明顯。在西伯利亞羱羊一家子好奇的目光之下,我們繼續躡手躡腳地在冰層上行走,相較之下,不旋踵穿越雪堆往山頂移動的羱羊家族,則顯得輕快優雅多了。
在某些區域,河川看似已然在新雪編織成的毯子下悄然融化,看起來旅程似乎將容易許多。然而,這一切都不過是幻覺而已,在轉了一個彎之後,河水愈發湍急,冰層則愈來愈薄,最後我們不得不改為攀岩前進。
獨特的冰雪之路
幾天前,來自藍登中學(Lamdon Model High School)的老師們陪著我開始了我的旅程,學校的所在地點正是位於與贊斯卡河交錯的夏達(Chadar)山谷。贊斯卡位於北印度的偏遠區域,坐落於大喜馬拉雅山脈與哈剌和林之間,亦介於喀什米爾與拉達克之間。拉達克在一八四二年前都是獨立的王國,後來被印度吞併,印度將自身的語言與文化強加於其上。在這片高海拔的沙漠之中,喇嘛寺院與為數不多的幾片綠洲彼此交錯,如同小型堡壘一般,俯瞰著同一條河流。
一月底,這裡的溫度在大喜馬拉雅山脈強勁的陣風肆虐之下驟降至-30℃;而一年間始終湍急的河水,也慢慢緩和了下來,直到被囚禁在冰凍的河床之下。這個時候,蜿蜒地向北往印度河合流的贊斯卡河,神奇地變成了一條冰之河。獨特的氣候現象,讓這座山谷的居民們在每年的十月過後便開始與世隔絕,大雪讓道路無法通行,而能與外界接觸、運送物資的唯一方式,便是從冰的上方步行通過。
我第一次造訪這條路是在五年前,當時是前來調查傳說中曾出現的「奶油商隊」,這個商隊主要運送的是大受好評的犛牛奶製成的奶油,這些犛牛(drimo)主要來自贊斯卡山谷上那座充滿靈氣、生機盎然的高山牧場。
那時我也遇到了許多來自印度各地的老師,充滿教育熱忱的他們別無選擇,每年只能走同樣一條冰河之路往返位於贊斯卡的學校,學校在每年三月的第一天──寒假結束時重新開放。這段在世上獨一無二的路途,與當地人在冬季那幾個月時艱苦的生活,深深震撼了當時的我。我下定決心,絕對要再一次回到這裡。
與世隔絕,教育不斷線
這些分布於贊斯卡山谷的村莊學校得到國際組織的大力援助,教師們的薪水多是由國際組織所支付。藍登中學便是其中之一,它在一九八八年由馬克.戴明(Marc Damiens)──一位愛上這片山谷與佛教哲學的法國人所創立,目前這所學校共有十二個班級,約三百名學生──其中約五成是女性,這所學校正是由一個義大利-法國的非營利組織AAZ (Aid to the Zanskar-Aide au Zanskar)贊助。
儘管這所學校是一所非宗教性的世俗學校,學校教授人文與科學課程,以及菩提語(在當地使用的一種藏語)、印度語、烏爾都語與英語課程,但佛教仍然是這間學校的主要特色。有些教師的身分為藏族的政治難民,因為中國對藏族的迫害而紛紛移住印度。
每位教師都希望能在開學前夕就提前返校預作課程準備,因此我與他們相約二月二十日會合。泰格是一位住在贊斯卡的本地居民,在這段旅程中將擔任我的嚮導,即使他十分風趣,在回答「Yes,sir.」時浮誇搞笑的發音引人發噱,但在幽默的外表下,仍能感受到他的些許不安。
在全球暖化的浪潮下,這幾年甚至連冰天雪地的喜馬拉雅山脈都受到了影響,特別是今年,氣溫從未低於零下,三十度(確定一下),造成許多地方的冰層在二月下旬都已經變得太薄甚至,以致冰層難以支撐人與雪橇的重量,增添了此行更多風險。
在我們出發前,我與體育老師拉吉夫及另一位已在夏達教了八年地理、政治學與藏語的藏族老師麥斯福,先行來到馬斯佛(Mathovu)寺院參加了一個非常特別的儀式。兩位僧侶讓我們進入lu-yar的深度催眠狀態(一種類似附身以傳達神諭的狀態),預言未來,也為新的一年祈福,我們與這些來自古老薩滿宗教的僧侶一同祈禱,希望為這趟充滿風險的渡河之旅尋到好兆頭。
在第一次的旅程,我總共花了六天才走完印度河到峽谷盡頭的整條路線,但對當地人而言,這件事根本用不上三天的時間。然而有時候也不盡然如此簡單,因為受到氣候異常的影響,冰的硬度有時能在幾個小時之內陡變,一片平坦開闊的區域可能一下子轉變為無法通行的漩渦。唯一能帶給人比較正向的思考是,這個過程極可能激發人類挑戰與冒險的精神,因為,與其一整天等待著路面重新結冰,還不如來場高風險的極限攀爬,試試自己的能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