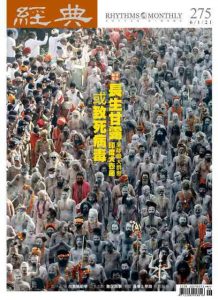近一年多的新冠疫情,確實是人類社會的一個大危機,其所造成更勝於戰爭的死亡人數,持久延續的經濟衰退和貧富加劇,國與國之間的尖銳對立,人際社會的猜忌不安,也都明顯可見,而在這些社會表象之下,有一個關鍵因素也值得討論,那就是科學形象的改變。
人類面對自然界中的流行疾病挑戰,在歷史紀錄中所在多矣,公認在中國醫學上有重要貢獻的張仲景,正是因為漢代流行疫疾造成大量死亡,乃有潛心戮力寫成《傷寒雜病論》之成就,也一直影響著中國醫學對於疾病的看法。近一、兩百多年來,因為近代科學興起,對於疾病的看法也多有改變,其中突發驟起的流行疫疾,更需要有「立竿見影」功效的科學來界定其徵,緩解其症,這回由新冠病毒的核酸解序比對,到藥物疫苗的開發施用,無一不是由近代生醫科學主導其思,主理其事。
近代生醫科學的基本思維就是科學思維,所謂「信徵驗實」,近年流行的「以證據為基準的醫療」。近三十年來,此種「實證醫學」大行其道,「實證醫學」依據的重要內涵,是許多生醫科學實驗研究的結果,以及因著這些研究思維而來的操作模式、因果關聯和統計設計,自然也創生出許多數據,證明這種醫療方式果然帶來了明顯的效果。
但是看似光鮮的表象之下,「實證醫學」也有其值得省思的盲點。在近代醫學研究上有代表地位的《新英格蘭醫學期刊》,去年刊出一個研究報告,調查一萬名在美國醫院接受「脈搏血氧計」測量的病人,發現非洲裔人的血氧飽和度通常會高估,一些血氧計測定出血氧飽和度在百分之九十二到九十六正常範圍的病人,改用動脈抽血測氧結果,甚至低於百分之八十八,這項研究報告指出,這種錯誤結果發生在黑皮膚人身上,要比白皮膚人高出三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