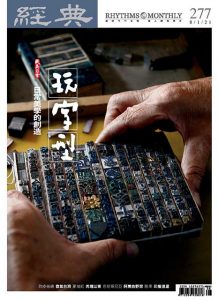當下人們談起科學,總有一種規制嚴整的印象,其實體制化的科學,年代並不算長久,在近代科學三百多年的歷史當中,恐怕最多只一百多年,到了十八世紀下半葉,如果看看公認為近代化學奠基者拉瓦錫當時的實驗室,其實無異一個廚房灶台模樣。拉瓦錫也算不上是個全職科學家,他還得靠其他的營生來支應研究,在羅蘭夫人口中所說「自由!自由!多少人假汝之名而行惡」的法國大革命後暴亂時期,拉瓦錫的被送上斷頭台,不是因於他的科學研究,而是他的營生侵害到另一政團利益所致。
一點不錯,其實科學發展的歷史從來沒有脫離利益的糾葛,科學被描繪成一種超凡出塵的面貌,其來有自。我們現在習焉如常的,以政府公共財政支持的體制化科學,可說始自上世紀二戰結束之後的美國,最近因為美國政府著力於科技競爭的投資,這段歷史又再受到了關注。
二戰期間擔任美國科學研究發展局長的電機工程專家布許(Vannevar Bush),得到美國總統羅斯福授權,撰寫了一份報告「科學——無窮盡的疆界」,這份在戰後發表的著名報告,開啟了世界各國政府支持科學研究的先河,迄今逾七十年。布許報告中強調的是科學研究的純粹性,主張政府應該支持科學著重研究科學基本問題,不為滿足社會需求。
雖然布許的提議後來得到社會與政治的支持,在美國成立了近代最早政府支持科學研究的「國家科學基金會」,但是過程也非水到渠成。因為當時另有一位石油巨擘後裔的參議員季哥羅(H.M.Kilgore),認為科學研究應該以解決社會需要為主要目標,布許想法的最後勝出有許多道理,政治妥協的成功策略也是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