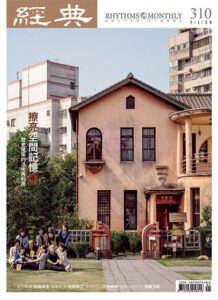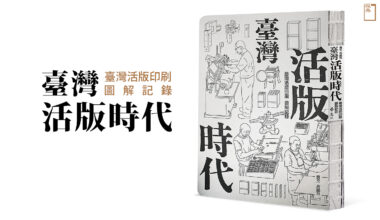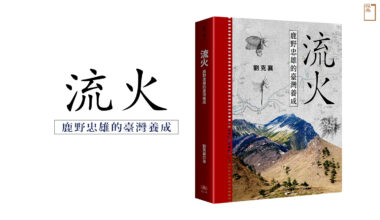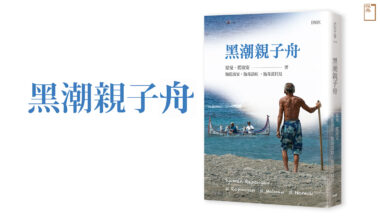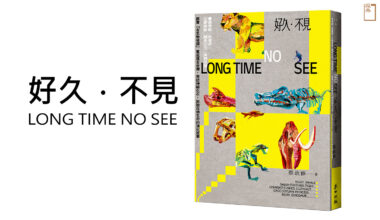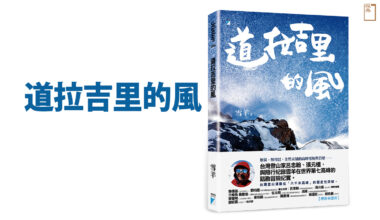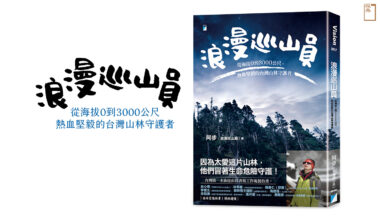二○二三年十月七日清晨,哈瑪斯無預警襲擊以色列,戰爭爆發,此後將近一個月在暴風中心的洪上凱,以無國界醫生身分站在衝突前線,他深知自己擁有這分依賴整體社會賦予醫者的特權,隨著任務開展,將看到的景象寫下真實存在於加薩的點點滴滴。
7/19 外國人特權
這幾天的加薩異常酷熱,本以為這是走廊的日常,但當地員工說這也是他們印象中幾十年來最熱的一個夏天。
加薩走廊的夏天幾乎無雨,天天都是晴空萬里的好天氣,每天出門前都會感嘆這天氣若是在台北,是最適合爬山的日子呢!但我這樣的想法或許有點太度假心態了,除了加薩境內根本無山可爬之外,長期被圍困的加薩也無法二十四小時供電,現有大部分的電力都從以色列境內支援,加上少部分卡達等有錢好朋友協助建立的電廠,但平均一天大約只有八至十二小時的電力,而且分區輪流供電。據說,在情勢緊張、以色列降低支援時,可能一天只有一兩個小時的電力。
今天一早遇到翻譯米娜時,她看起來睡眼惺忪。問她怎麼會這麼累?她說因為房間太熱了,昨晚只睡三個小時。我好奇地正要問她不是有電風扇?並接著誇耀初來乍到的自己很適應這樣燠熱的天氣時⋯⋯
「沒有電啊!」米娜說。「昨天一直到半夜四點,我們那區才供電兩小時,開了電扇才睡著。」
聽到這裡,我把嘴邊的話吞了回去。還以為自己的適應力多強,多與加薩人站在一起,卻徹底忘了自己所在的住所是有發電機的,完全是何不食肉糜的心態而不自知。
這讓我想起之前曾在書上看到expat privilege這個詞外國人特權,有些更極端的寫法甚至會冠上white,white expat privilege——白種外國人特權。
以為自己多麼英雄式地進到前線,但更可能的是享有了外國人紅利,住在比較安全的區域,隨時隨地得到不一樣的關注跟保護,話語權也更被重視。甚至就本能地認為自己的經驗具有普遍性,但這一切的成本所帶來的效益,是真的足夠、值得的嗎?
或許因人而異,也或許因為有太多隱形的利弊難以評估,但更重要的可能是身為外國人、身為人道救援領域的工作者,隨時要有認知,不要帶著「我來幫你」的英雄式心態。
對我來說,這經歷真的更像是因為醫生身分而能到一般人無法抵達之處。而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我還能做出一點點正向的改變,那就太好了。
7/20 印尼醫院
今天的一項重點行程是拜訪印尼醫院,在此之前我必須先等待巴勒斯坦醫師執照申請生效,而印尼醫院就是我即將工作的主要醫院;之所以如此命名,是因為這家醫院是印尼人民捐贈的,它是北加薩最大也最重要的醫院之一。雖說最大,整體規模大概類似台灣的地區醫院,但所負擔的人口卻是遠超過其能量的數十萬人,所以據說整個醫院都呈現嚴重過載的情形,而其中又以急診室最為嚴重,原因跟長期戰亂還有民眾對基層醫療系統的不信任有關。
接著,我和幾位單位主管一起拜訪阿塔爾醫師,他是在加薩衛生部裡主管急診業務的領導人,本身也是急診科醫師。他在早期巴勒斯坦地區還沒有醫學院時,被送到烏克蘭讀書和受訓,貌似是腦袋清楚的人;根據辦公室前人留下的紀錄,也對他的評價很高。昨天聯繫後,今天馬上就約時間且劍及履及地跟我們一起和印尼醫院的行政團隊開會。
今天與會的無國界醫生人員,有專案總管海倫、醫療統籌達爾文、醫療支援蘇賀柏跟我。巴方則有阿塔爾醫師、印尼醫院院長以及急診主任沙班醫師,還有幾位沒有表明身分的人。
根據前幾次經驗,就算是很純粹的技術性會議,也都會有其他單位的人列席,我猜想可能是政治領導其他專業的組織結構,但至少目前為止我遇過的幾次,並沒有受到嚴重干擾。
會議結束後,沙班醫師帶我們參觀了急診室。在此之前,我從當地同事還有評估資料中,已經知道加薩走廊人民使用急診的大概情況。以印尼醫院為例,急診每日來診量四、五百人,這個數字只比林口長庚醫院略少一些,但印尼醫院的整體規模連林口長庚醫院的十分之一都不到。
同一時段有四位醫師,而林口長庚的正常配置是兩三倍以上。以上計算都還沒考量到在台灣的醫院是訓練成熟的急診專科醫師,但在加薩的醫院,幾乎都是醫學院剛畢業、臨床經驗稀缺的菜鳥醫師。
而資料分析認為,加薩人民之所以這麼依賴急診系統,有幾項可能原因:第一是這裡的初級照護系統(診所等)很稀缺,而且只要治安情勢稍微緊張,就會全面關閉,因此連年戰火也養成加薩人凡事往大醫院跑的習慣。
另外一個原因是,政府慣壞民眾的瘋狂醫療政策,一年只須繳費數十美元,就涵蓋大部分的醫療費用,去急診就醫只需要台幣一、二十元就全包,所以來診包含許多輕症病人。
分析認為這跟哈瑪斯組織最初始的慈善性質,以及後來用此一手段贏得人民支持的方針有關。
而這個現象很大程度地排擠了急診系統原本被設計來處理真正急、重症病患的能量,也讓原本應該負起責任的基礎醫療永遠發展不起來。但此一現象隨著持續不斷的戰事,已歷經數十年且深深嵌入社會文化之中,要想改變,會是個非常棘手的問題。
同時,讓我充滿期待的是,印尼醫院正處於一個即將改變的階段,新上任的急診主任沙班醫師,剛從西法醫院完成第一屆的急診專科醫師訓練,是加薩本地第一批急診專科醫師,而他也很想引入包括檢傷系統等改變流程的制度,但他的經驗和擁有的協助都很不足,因此他很高興也很期待我們的到來。而對我來說,這可能也會是難得的機會,得以參與一個國家急診系統基礎但至關重要的建置。
7/21 教育普及
今天是伊斯蘭曆的新年,放假一天,剛好接著週五、週六而成為連假。神奇的是,在我剛抵達時就聽說會有這個假期,但日期還未決定,因為伊斯蘭傳統律法要由神職人員觀月後決定實際日期,所以一直到前兩天,政府才正式宣布今天為假日。這對於從一個前一年新聞就會整理好「明年怎麼請假才能放最多天」的國度而來的我來說,也算是一種文化衝擊。
另一件有趣的事情是,今天也是當地高中畢業、公布成績的日子,而慶祝的方式是happy shooting(歡慶式的射擊),當地政府特別允許群眾可以在特定的時間內對空鳴槍慶祝,於是在這段時間裡,我們被組織要求一定得待在室內以防意外,而我也就打開窗戶享受陣陣砲火聲伴隨著歡慶鼓譟的聲響。
來加薩後很讓我驚訝的一件事,就是這裡的人非常重視教育,高等教育的普及率也很高,或許是因為這一地區自古以來就是文明薈萃的地方,聯合國多年來也投注了許多資源在當地的教育上,但有當地人半開玩笑的跟我說「因為我們在這無事可做」。有點悲傷,除了被禁錮之外,加薩的整體失業率將近五成,年輕人失業率更是突破天際的七成,許多人無法找到工作就繼續讀書,到真的必須出社會時,也只能在街上徘徊遊蕩。
以色列的設想是讓當地民不聊生,接著民眾會開始把矛頭指向掌權的哈瑪斯;這個策略或許部分有用,但在已經歷了幾十年封鎖的今天,仍然看不見一絲曙光。
8/28 失控的急診室
無國界醫生在加薩的急診室裡有個很重要的任務,就是推行檢傷制度。在台灣,檢傷制度推廣已久,大部分民眾也都能接受急診室處理病人是依據嚴重度而非先來後到,但巴勒斯坦除了急診專科的概念還在萌芽階段外,當地民眾對於急診的功能與認知,也都還存在著很多誤解,而這或許也跟政治背景有關;在巴勒斯坦,什麼事都離不開政治。
在加薩主導的哈瑪斯,早期其實是以伊斯蘭律法為準則的慈善團體,在公機關失能而社會又動盪不安的情況下,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哈瑪斯數十年前發源自加薩走廊,跟具有類似慈善性質的埃及穆斯林兄弟會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因此,公眾的急難救助、教育支援與醫療協助,是哈瑪斯早期發展的根基,也藉此在群眾之中立下很好的聲譽。由此脈絡發展出的醫療體系,跟慈善有很強烈的關聯,因此民眾也養成了有任何小病痛就衝到醫院的習慣,而醫療體系也對民眾的索求概括承受,這當中有些可能有理,但人性導致了大部分是無理的要求。
我所在的急診是加薩北部最大的醫院,但急診室同一時段約三、四名醫師要同時處理上百位病人,其中大部分是可以在門診或診所處理的輕症病人,但本地的就醫習慣就是往急診室衝,因此高峰期的急診室常常被輕症病患癱瘓。
曾經有其他的國際組織試圖協助發展基礎醫療設施來紓解急診室的壓力(現在也還在繼續推廣),但民眾觀念已根深蒂固,政府又不太願意使出更強硬的手段介入,畢竟哈瑪斯就是從草根群眾出發,因此想到的解方反而是擴大所有急診室空間,但理應要同時並行的急門診措施,卻因人力不足而遙遙無期,導致有更多的民眾反而因環境寬敞舒適而更樂於在急診室久待。
在最深層原因沒辦法有效解決的現況下,一套有效的檢傷系統至少能夠協助快速準確的辨識出嚴重的病人,以利早期診斷治療。
但加薩的現況是幾乎沒有檢傷系統,病人掛完號便擠到人滿為患的護理站前,說話比較大聲或性格比較兇悍的病人、家屬,便能較快獲得治療,老弱傷殘以及真正的重病患者都被擠到角落。因此我們評估認為,如果能夠在加薩的急診建立起有效的檢傷系統,然後再進一步讓大眾了解急診的目的與功能,一定可以讓急診系統更好,順利救治更多的病人。
10/7 燃燒的加薩
首先會在空中看到帶著黃色亮光的飛行物,而飛行途中灰色煙霧開始從尾部擴散,之後才是聲音。
當你剛意識到眼前高速飛行的物體是火箭彈時,姍姍來遲的音波這就抵達,類似某種戰鬥機高速飛過的渦輪聲。
而當你準備捂上耳朵時,卻被眼前飛行物爆破瞬間發出燦爛火光的一剎那吸引住。
那是鐵穹系統射下火箭彈的瞬間,所以你忘了捂上耳朵,接著爆炸巨響灌入耳膜。
戰爭在完全沒有預期的情況下開打,本以為前陣子的抗爭已達成共識,以色列的長假已過,看似最緊繃的情勢已然消緩。還記得昨天看到以色列的社論稱讚經濟的放鬆讓加薩比以往都還更加穩定云云,但就這麼突然的開始了。
清晨時分被陣陣悶響吵醒,睡夢間以為又是另一次火箭彈試射⋯⋯
一下、兩下、三下⋯⋯
我陡然醒來,接著是數不清的連續聲響,這次是真的開戰了。
我走出房門要去找住在對面的專案總管馬提爾斯時,已看到他愁容滿面的正試著釐清狀況。他恍惚的對著我說:「不是往海上射,而是特拉維夫的方向,這次非常嚴重⋯⋯」
「到安全室集合!」這是唯一傳達的指令。
在加薩地帶,無國界醫生有許多安全規範及防範措施,包括辦公室、住所以及車輛,都與以色列、巴勒斯坦雙方分享位置及GPS訊號以免誤炸,屋頂覆蓋巨大的組織旗幟以防空襲。
但加薩人口密集眾所皆知,而哈瑪斯也刻意將軍事機構設置在人口密集處,所以以軍瞄準的目標常常和民宅相距不遠,因此無國界醫生在加薩的建築物都設有鐵窗覆蓋的安全室,每道窗都被加上了厚重的金屬保護板,使得這個空間在此刻讓人覺得更加冷酷。不過這裡是建築物內最安全的地方,因此大家也都待在裡頭,試著休息。
隨著情資的揭露,我們得知這次是前所未有的事件,哈瑪斯及其友軍不但從加薩境內發射數千枚火箭彈,而且是朝著特拉維夫及耶路撒冷的方向攻擊,這是很明確的宣戰。
更糟的是,數千名武裝人員透過海陸空,潛入以色列南部多個城市,攻擊以及綁架包括平民在內的人質,據傳不但攻陷了重要的艾瑞茲關口,占領了二十多個南部城鎮及定居點(kibbutz),還擄了數百名人質進加薩。雖然哈瑪斯宣稱他們的目標都是武裝人員,但國際普遍認為包含了許多平民,而這顯然嚴重違反國際法。
以上這些都是前所未見的,而且都直接讓情勢急遽升溫。
我平時工作的醫院在加薩北部,距離加薩中部的無國界醫生住所大約有三十分鐘車程,就算是平時的交通,也都需要以巴雙方核定。而在這個戰爭開打的時刻,根本無從協調,因此我們被告知先待在辦公室不要前往醫院,但就在稍後的中午傳來可怕的消息,我工作的印尼醫院疑似被襲擊,造成醫護人員傷亡,目前還不知道為何以色列瞄準醫療設施攻擊(後續證實當次事件是醫院周遭設施遭到攻擊)。
一位朋友傳給我罹難同事的照片,是位友善的年輕急診護理師,前天才跟他一起工作,每次見面都很熱情的握手擁抱,略懂英文的他也常常協助我們與病人溝通,他是位不過二十多歲的陽光青年,實在很難想像前幾天活蹦亂跳的人現在冰冷的躺在擔架上。總說戰爭殘酷,但實際有認識的人因此而離開,那酸澀的感覺實在難以形容。
今夜的加薩已經開始燃燒,成百上千的病人或死或傷,擠滿了西法醫院。而慣例歌詠烈士的遊行聲勢更為浩大,或許是因為一次有太多死者,而加薩民眾的情緒也已被點燃,或喊或歌的喧囂不斷繞著醫院行進,本應平靜的週末夜晚被注滿了復仇的情緒。
而在這片喧囂聲中,空中盤旋的無人機依舊默默的看著。
我實在很不想這樣預想,但如此燃燒的加薩,接下來的這幾天到底會遭受什麼樣的報復呢?
10/11 見證與發聲
因為情勢的演變,現在要去位於加薩北部的醫院工作已不可能,因此我們試著轉移至中南部其他和無國界醫生也有合作關係的醫療機構,持續人道救援的任務。
另外,許多外籍員工在援助專案裡原本就以監督及協調為主,因此也持續忙碌著。專案總管從第一天開始就忙得不可開交,除了要隨時更新情資,掌握大家的安全(包括外籍及本地員工),不時向總部回報及求援外,還要盡可能維持原本的業務運作。從爆發衝突以來,我幾乎沒看到馬提爾斯在睡覺。
醫療統籌達爾文的主要業務也是協調,調度資源、確認量能,還要關心組織內員工的身心狀態。各成員都盡全力用著不同的方式持續工作。看到大家深陷在衝突及巨大壓力下還能持續工作,真的由衷敬佩,而且也更切身體會了無國界醫生的精神。
團隊每天還是維持開會,先更新情勢後就進入業務內容,過去一天我們做了哪些事,還有哪些缺口可以協助,最後才是關於撤離的資訊更新,優先次序的輕重拿捏真的很困難。而其中最忙的,就屬其實是短暫來加薩出差的媒體經理路易。
無國界醫生和其他人道救援組織有一項很不一樣,也是我們秉持的特點,就是組織準則裡的「Témoignage」,中文譯為「見證與發聲」。雖然無國界醫生的初始及核心任務都從醫療需求出發,但很多需要人道救援的情境其實都不是單純的醫療問題,特別是武裝衝突大多和地緣政治、社會結構有關,單純關注醫療問題並不能有效解決,而身為醫療人員,常常獲得某種能夠身處衝突現場的「特權」,因此除了盡醫療的本分外,我們也認為將看見的事情說出來以期獲得重視,甚至進一步發展出解決方案,也是非常重要的使命。因此,負責公關資訊的路易也開始串聯各大媒體、安排採訪,希望能將加薩內的第一手消息傳遞出去。
這幾天我主要忙於調整一項處理大量傷患的計畫,原有的計畫在部分區域遭受空襲以及許多醫療人員無法移動到醫院的情況下,已不可能實行,因此我們試著將其他單位的量能集中到關鍵的中重傷急救區,同時調整周遭醫院接受轉診的條件,希望在交通許可的前提下,分散該醫院的負擔,並且安排人員引導上千名在醫院避難的居民、移動到適當的區域,讓原本混亂失序的醫院得以整理出基本的動線,要集中資源、維持一定量能,並聚焦在治療效益最大的病人身上。
稍早,馬提爾斯交付我一項臨時任務。有傳言說以軍開始使用白磷彈攻擊,他希望我搜集一些相關的醫療資訊以備不時之需。對此,我只有耳聞,但從沒治療過這樣的病人;隨著搜尋結果,各種怵目驚心的資訊迎面而來,燃燒彈、深層灼傷、七成致死率、國際禁用。希望只是傳聞,沒理由在已經幾乎一面倒的戰爭裡使用這樣不人道的武器;況且在人口如此密集的加薩,受傷最重的只會是一般的平民。
10/20 漫無止境的等待
在車內看著天上的雲幾乎沒有移動,整整盯了十分鐘,雲還是在遠處維持著一樣的位置與形狀。
戰爭進入第十四天,我們在此處的第六天。中午前後這段時間豔陽高照,人們躲在少數的遮蔽中數著時間。來自亞美尼亞的娜娜,今天早上沮喪的跟我說,她發現自己從每天每天可能移動的期待,變成了每分鐘每分鐘的盼望。這不是個好現象,當你有太多次的期待時,就得面對更多次的落空,以及伴隨著高低起伏的情緒,但又很難在這樣停滯的時刻停止期待。
慢慢的,已經開始習慣砲火聲,甚至昨夜據說有一次造成車輛震動的近距離空襲,但我連醒來都沒有⋯⋯
挑戰漸漸轉變為漫無止境等待的心理煎熬。目前飲水、飲食都算穩定,但網路以及跟外界的聯繫幾乎為零,被困在一個不舒服、不安全且一無所知的環境中,真的是不太容易。對我而言,有幾個最難熬的時刻:第一個是一早起來發現又是新的一天要面對而有點惆悵,再來就是近午時刻一切活動都停擺,大家紛紛找自己的樹洞潛伏、療傷。但隨著日落,大家又開始活動,互相砥礪面對新的一天,而晚上也是預期不會有新消息的時刻,所以也能更篤定的度過。
昨天和瑞吉聊天,他來自菲律賓,目前定居羅馬,是無國界醫生巴塞隆納行動中心的專案協調。我很喜歡他處變不驚的穩定情緒,以及總是關心大家的微微溫暖。
唯一一次見到他有較大的情緒,是跟總部有不同意見時,他邊講電話邊大力踢了顆路旁的石頭。跟這樣有豐富經驗的組織成員聊天,總是很有趣。昨天他提了幾個很有趣的觀察,譬如「新冰箱症候群」,描述許多無國界醫生的成員在經過了任務的大風浪後,回到原本的家人朋友生活圈,儘管努力敘述分享,但極端的情境總是很難述說,而家人朋友們無法共感,聽到一半就把話題帶回他們更熟悉的那個新買的冰箱,隨之而來的失落感跟任務的艱困程度成正比,而他很擔心這次這麼特殊的任務會造成很巨大的失落感,特別是像我這種初次出任務的人。
另外他也提到雖然無國界醫生已有一組新團隊在開羅準備和我們交接,一旦關口打開,就會進來加薩接續任務,而基於心理健康考量,總部要求原本團隊內的所有外籍人員都先撤離,不過他很想留下,他已在加薩出過七次任務,而且考量到現在情境十分複雜,如果有原本就在加薩的人留下,會讓全新團隊開始得更有效率,但無奈他無法改變決定。
相較於此,他提了紅十字國際委員會作為對照。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比我們更早決定方向,並開始準備下一階段的工作,他們已在加薩南部覓得新的辦公室,且已開始評估各種介入方式,一旦關口打開,便能快速反應,而且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留下數位核心團隊成員作為開展的重要動能。瑞吉認為,在這個最壞的時刻,對人道救援組織來說其實也是最好的時刻。
他還提到了見證與發聲這件事。無國界醫生跟其他組織不同且引以為傲的,就是我們認為說出看到的事情非常重要,因此我們也做了很多採訪、聲明,甚至譴責。但是在發聲和評斷之間的界線很難掌握,我們畢竟還是以提供人道醫療為主的團體,我們說出看到的事,但是非判斷應該是我們要做的嗎?我們有能力查證嗎?這麼做的後果會是如何?例如前幾天傳來的醫院遭攻擊事件,誰攻擊的?為何會被攻擊?其實組織本身並沒有足夠的能力徹底調查,但如果在現場目睹的我們不在關鍵的時刻發聲,世界會知道嗎?等到所謂清楚的調查後,一切不會太晚嗎?做與不做、怎麼做以及甚麼時間點做,真的有太多的影響與後續效應了。
11/3 不會忘記加薩
躺在飯店柔軟的床上,一切都很不可思議。已經抵達開羅一天多了,但還是持續在適應兩種極端環境的差異。衣物幾乎都遺落在加薩,昨晚走去隔壁的服飾店要買幾件衣服,看著貨架上琳瑯滿目的物品,突然覺得頭暈;油腔滑調的店員試著多賣幾件,光是這樣簡單的行程,就已讓我身心俱疲,只得回到房間休息。
已經好幾年沒做夢了,但昨晚做了個夢,沒有很具體的情節,不過依稀記得是個一直往下墜落的惡夢,混雜著不安、焦慮、無能為力。做這夢的原因有可能是跟前幾天的地板相比,這高級飯店的床太軟太舒服了,而更可能是在加薩的這二十六天裡,無法掌握的情況太多,這種抓不到支點的感受,強烈到讓人感覺無助,但生存模式下只能暫時將這種感覺深藏,隨著壓力釋放,慢慢的從潛意識裡開始償還。
本來以為順利離開加薩,遠離戰火、恐懼及窘困生活環境的我,會感受到無比的開心和喜悅。確實有種如釋重負的感覺,知道家人、朋友不必再每天提心吊膽的追著戰爭新聞的細節為我擔憂,這讓我感到安心,但想像中的喜悅卻被巨大的罪惡感取代,我安全離開了,但我早已與這片土地以及生活在上面的人們產生連結,能夠沒有憂慮的走在街頭,能夠選擇午餐要吃什麼,能夠每天洗澡、喝到乾淨的水,我很幸運,但這一切都提醒著我,我的朋友、我的加薩朋友,以及超過兩百萬的加薩居民們,仍然深陷在戰火之中。
這種現實又抽離的感受,讓我深深感到不安。
無論戰爭怎麼持續發生,地球依然轉動,世界如常運作,但我們仍須持續關注發生在世界上各個角落的苦難。人道主義是對苦難的慈悲反應,是對處境最困難的人們關注且伸出援手。至於加薩,我會持續的寫,持續用我自己的方式,對這塊與我已產生特殊連結的土地與人,保持關注。
本文摘錄自玉山社出版之《加薩日記:來自台灣的無國界醫生前線人員在加薩的第一手見聞》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