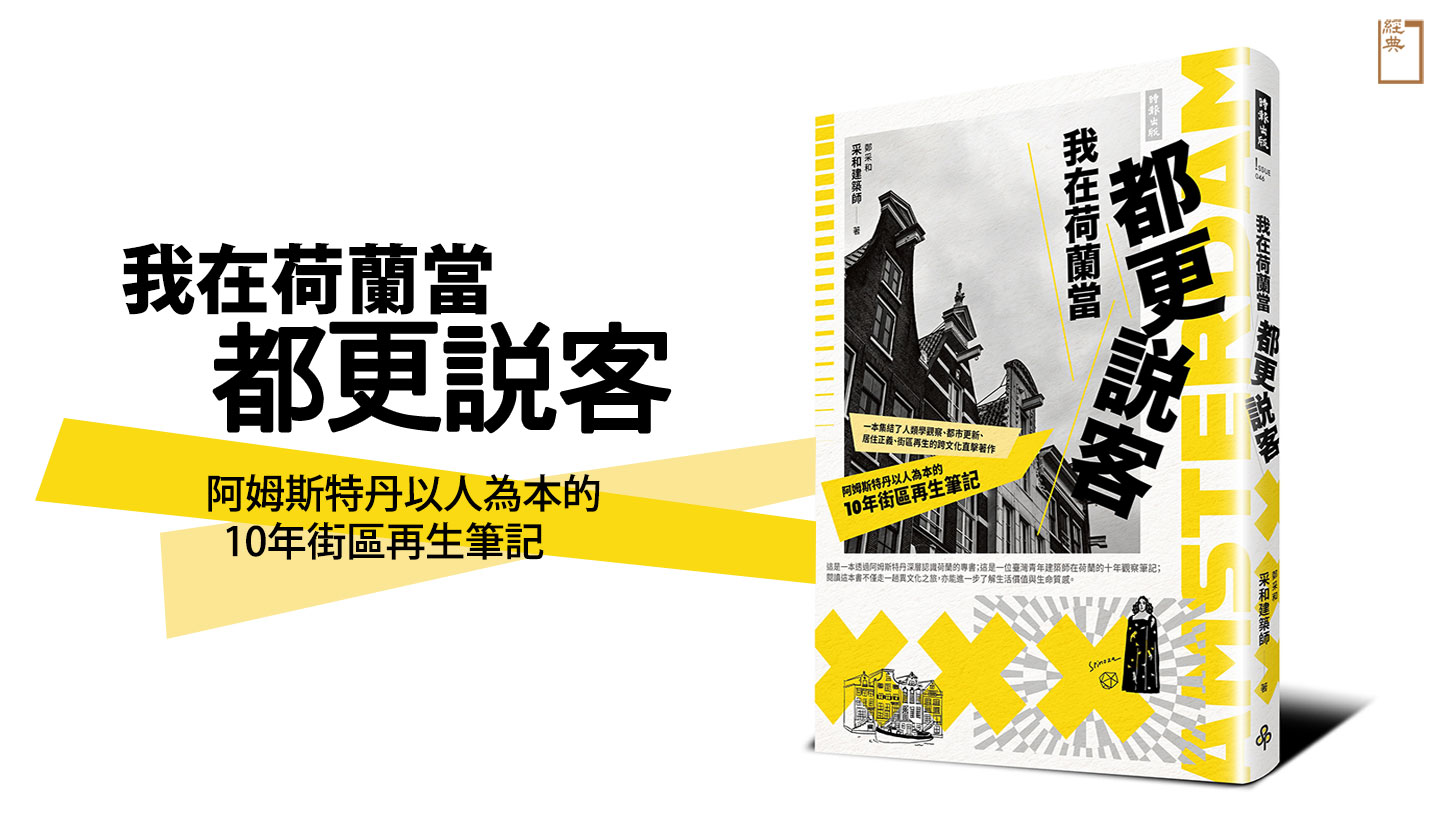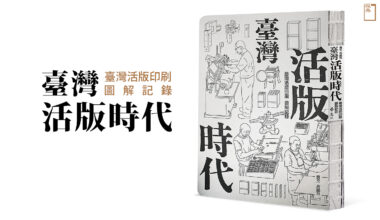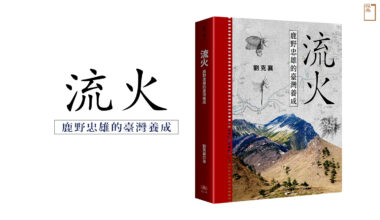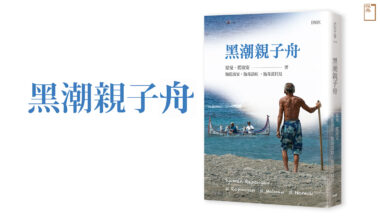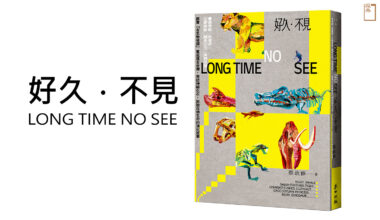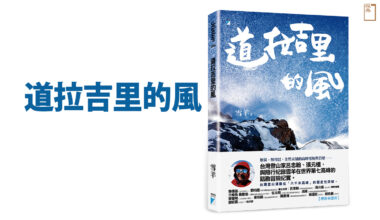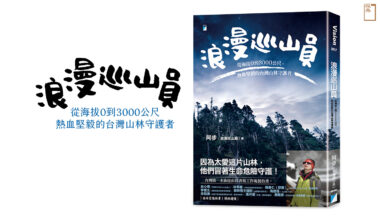近十年來,台灣社會陸續有一些改變,從太陽花學運開始,社會改革的呼聲不斷,諸如房價高漲導致年輕人買不起房子、資源分配不均產生勞資糾紛……,這些社會現象使得新一代的公民希望對大環境及體制進行重新檢討,這些覺醒也反映在這些年的學生運動、罷工運動及政黨輪替等方面。
荷蘭是一個追求個體自由又講究社會秩序的國家,而阿姆斯特丹又是其中的代表城市。阿姆斯特丹的城市發展,就是一段個體自由跟社會秩序之間不斷拉扯的動態歷史。早在十七世紀,阿姆斯特丹人就已經逐漸擺脫君王的極權統治及教宗的領導,開始實施地方自治,也就是在那個時代,阿姆斯特丹人開啟了理性思辨並且成為自己的主人。與海爭地與治水的經驗(家家戶戶的農人都需要參與)讓阿姆斯特丹人習慣於合作、團體協商及城市規畫的公民參與。
徘徊在自由與秩序之間的各種衝突與妥協經驗,讓荷蘭人不拘泥於政治意識形態,而能在困境之間尋找務實的解決之道。這些經驗充分反映在他們的社會福利政策、住宅政策、城市規畫及建築設計上,是荷蘭社會不斷向前推進的原動力。
以阿姆斯特丹來說,每項都市重建案,都是經歷十幾年以上的公民協商成果,這樣的城市再發展速度比起台灣城市是慢太多了,尤其是部分都市街區又經歷了現代主義城市規畫的失敗歷程,後續的都市重建及住民重組又花了一整代人的時間再重新來過。相較於台灣人耳熟能詳的「都市更新」,僅聚焦於一棟建築物的重建或是「一坪換一坪」式的利益兌換,希望阿姆斯斯特丹式的都市重建及街區再生故事,可以提供給讀者跳脫於現狀的思維並引起對公共環境的關心。
翻轉床
從鹿特丹(Rotterdam)的貝拉格建築學院(Berlage Institute)畢業之後,我搬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住在舊水管區(荷:Oud Pijp/英:Old Pijp)一戶大約八坪大小的小套房裡。舊水管區是阿姆斯特丹著名的酒吧區。從阿姆斯特丹中央火車站搭乘電車,穿過十七世紀環狀運河區之後,看到海尼根博物館(Heineken Museum),就到了舊水管區。世界盃足球賽季的夏天夜晚,我常常因為街上的喧鬧歡呼聲穿透過僅有單片玻璃厚的木窗而被吵得睡不著覺。舊水管區有一條全阿姆斯特丹最大的市街——阿爾伯特市場(荷:Albert Cuypmarkt/英:Albert Cuyp Market),而我居住的街道——戈弗特.弗林克街(Govert Flinckstraat)就位於阿爾伯特市場街道的隔壁;這條街上的住宅一樓常常作為市場街的倉庫,存放著市場的攤車。清晨五點就開始會有攤車進進出出,攤車壓在街道的石頭鋪磚上會發出轟隆轟隆的聲音,也會把我從清晨模糊的夢中吵醒。在這棟破舊的小房子裡,只要任何一個住戶被按電鈴,其他住戶也都聽得到。自十九世紀末,這一區居住著大批工人階層居民,一家四口就擠在我所處的小公寓裡居住著。當時,連同我在內,這棟房子總共住著六個人,每層樓兩個小公寓各住一個人,分前後間的套房。由於隔間的施工非常簡略,只有薄薄的木製三明治板輕隔間,除了視覺上看不到對方外,從聽覺上都知道彼此早上什麼時候出門,晚上多晚回家,甚至對面住戶沖馬桶的聲音都聽得到。
從這棟建築物的隔音效能可以感覺出這裡以前曾經是一個建築品質很差的勞工住宅區。現在住在這裡的居民中,有四成以上是非西方國家居民,此區擁有大量的社會住宅及社會租金住宅,混合著住在高級雅痞小公寓的年輕歐洲青年學生及社會新鮮人。街上雖然很多新潮的酒吧、餐廳及設計師工作室,但也參雜著少數族裔特色商店、洗衣店、五金行及腳踏車店。
「嗶……」海恩.德漢(Hein de Haan)按了我家樓下的電鈴,「如雷貫耳」。自從去年我邀請海恩來我家參加我的生日派對後,他就跟我提過幾次他的大女兒以前也住在舊水管區,因為公寓一樣是小小的,放一張床就幾乎半滿了,所以他特別製作過一張翻轉床。白天不需要床的時候,將床往牆壁輕輕一抬,就可以增加活動空間。他大女兒結婚後,這張床就收進他的儲藏室,很多年沒動過了。我入住這棟小房子後,的確苦惱了三年,老想著怎樣騰出更大的空間可以讓自己活動或是工作,後來終於忍不住催促海恩,希望他把他說的翻轉床盡快給我。
聽到電鈴聲後,我連忙下樓幫忙搬運這張翻轉床。這棟十九世紀興建的工人住宅公寓,就像很多經濟實惠的荷蘭住宅一樣,為了節省樓梯所占的樓地板面積,樓梯斜度大約是五十度,走起來非常危險。早年為了將這張雙人尺寸的翻轉床搬上舊水管區的小套房,海恩將床架設計成可以完全分解的系統,床板的鋁製外框可以拆分成兩個部分——上下兩個ㄇ形,組裝起來就成為一個口形,鋁製外框是中空的,可以減少重量,盡量讓使用者翻轉時可以感到輕鬆。為了讓兩個ㄇ形的鋁框可以結合,海恩在鋁製外框中間插了一支木棍,這樣一來,上下兩個ㄇ形的鋁框就可以互相套入。為了將鋁製外框套進木棍,安裝者需要用錘頭敲打。因為這張床已經拆拆裝裝過幾次了,所以敲打處可以看出鋁製外框已經有些變形。床架安裝好後,我跟海恩下樓將綁在他的中古廂型車車頂上的雙人床墊取下,準備再次費勁地把床墊「擠」進狹小的樓梯間上三樓。這時隔壁棟的鄰居剛好走出,向我們多望了一眼。海恩向我眨眨眼,笑說:「我想路上的人看到一位白髮老翁和一個年輕東方女孩一起抬一張雙人床墊上樓,一定會有很多遐想。」
船屋
阿姆斯特丹著名的船屋,也跟舊水管區的歷史一樣,一開始是在十九世紀時,為了承接大量由鄉下擠進城市的離農難民潮而產生的住宅供應應急方案。那個時候為了讓新來的居民(主要是吉普賽人)有居住的空間,政府決定將水上的泊船位劃定出來,以容納船屋並酌收水上產權費,提供住不起陸地房子的窮人來住。一直到一九六○年代左右才開始有了相關進一步的管制規範,因為符合當時的社會氛圍,所以當時很流行住在水上,因而改裝船屋也突然變得興盛了起來。擁有船屋的人必須先向市政府申請停泊證(荷:mooring permit/英:parking permit),也要像陸地上的屋主一樣負擔汙水處理跟垃圾清潔等稅費。時至今日,阿姆斯特丹的水上船屋,儼然成為本身獨有的城市風景及生活情調的代名詞。根據官方估計,目前阿姆斯特丹總共有兩千兩百五十艘船屋,其中停靠在市中心的共有九百艘。此外,由於運河上的泊船位有限,泊船位的價值也因此水漲船高。跟很多阿姆斯特丹人一樣,海恩也有一艘引以為傲的船屋。截至前幾年,海恩才將他的船屋出售,船屋本身沒賣多少錢,反而是他的泊船位賣到大概二十萬歐元(相當於新台幣八百萬,約是台灣一間小公寓的價格)。在二十年間,產權價格自他購買時的一萬歐元上漲了將近二十倍。想想,阿姆斯特丹的「陸上地產」因為建立了完整的社會住宅體制,所以這麼多年來價格的漲幅不算太高,但是「水上地產」的飆漲程度,反而因為政府沒有介入,所以跟我們亞洲國家的地產一樣——漲得瘋狂。
水上的船屋其實可以歸類為三種:
第一種是一般的飄浮住宅,就是一個家,坐落在一個平台駁船上,靠水岸停靠,自身沒有航行移動的能力(荷文及英文裡皆稱為Ark)。
第二種其實就是艘船,自身可以到處移動,上面附個小室內座席及駕駛艙,但其實沒有辦法長期住在裡面(荷:Schip/英:Ship)。
第三種,是最有趣的一種,就是可以航行的船形房屋,形狀比較長,甲板空間的屋子裡大概可以容納二到四人起居及睡眠,其實可以算是一個移動的家(英:Converted Ship or Schark)。
「亨德列克碼頭」(Hendrik Marina)是一艘長期停靠在王子運河旁、有著一百年歷史的船屋。從二十世紀初開始就由不同的船屋主接手居住及管理,這其中包含有詩人、航海家、音樂家(因為在裡面練習音樂不會吵到其他鄰居)等。雖然感覺生活狀態非常浪漫,但其實每天都要修修補補的,沒有外面看起來這麼的浪漫。目前這艘船屋已開放作為阿姆斯特丹的船屋博物館,在裡頭,訪客可以親自感受到住在大型船屋內的感覺。
船屋裡的廁所設計,因為沒有接到陸地的排汙系統,思考模式也和我們常態性的做法完全不同。譬如廁所會將屎尿分離,讓尿液隨著汙水排到岸邊的接收管內。糞便則會固態化,將其中水分也分離到尿液的處理器那邊,然後乾燥固化的屎塊則可以定期收理,並有專業的收糞袋可將糞便塊體收集後帶到公共垃圾桶丟棄。
聽海恩敘述他及他兩個女兒在船屋上的生活經驗,其實解放了不少我這個慣於在陸地上生活及規畫的建築師的想像力。夏天,海恩在兩個小孩放暑假時,會帶著一家人行駛他們的船屋,到小島上無人的沙灘旁停靠留宿個一至二週。到岸後,將置於船內的腳踏車拿出來,變成一家人在小島上的交通工具。當食物不夠時,爸爸就再將船開回小鎮補充糧食後再回小島。渡完假,再把船屋開回阿姆斯特丹市區,非常方便。此外,週末一家人可以開著船屋到處去玩,有時候玩得太盡興,星期一的早上,海恩為了讓要上班的太太或要上學的小孩可以睡久一點,會直接將船屋就開到太太上班的地點或是小孩上學的學校前,讓她們起來盥洗之後就直接進公司或到校,實在是太方便了。
還有一位演員朋友常常夜夜笙歌,經常就開著他的船屋到處開趴。據他說,他有很多朋友也擁有船屋,所以如果其中一人開趴,大家就把自己的船屋開到開趴那個人的船屋旁邊夜泊。到了大半夜,大家已經醉得差不多時,就直接跳回自己的船屋躺平,不需要麻煩朋友、也不需要住旅館,更不用擔心酒駕,一樣也是相當方便。
海恩說:「在九○年代某年中,有一回,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為了減少運河上的船隻流量,所以宣布了一項法令,第三種船屋(可以行駛的船屋)不算是船,所以船主必須將船屋固定駐泊不能行駛,只讓第二種船屋(其實就是艘船)在市區內的運河行駛。沒想到才一宣布,就被擁有可以行駛的船屋的船主大罵。為了表示他們的憤慨,為了證明自己擁有的也是一艘船,兩百多位船主在一個星期天集結,一起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的運河上『遊船』抗議。因為船數眾多,他們形成了一條很長的抗議隊伍,讓很多座拱橋得要同時打開以讓這些船屋經過,此舉就癱瘓了市中心的陸上交通。據說自此之後到今時今日的二十多年間,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就再也沒提過這個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