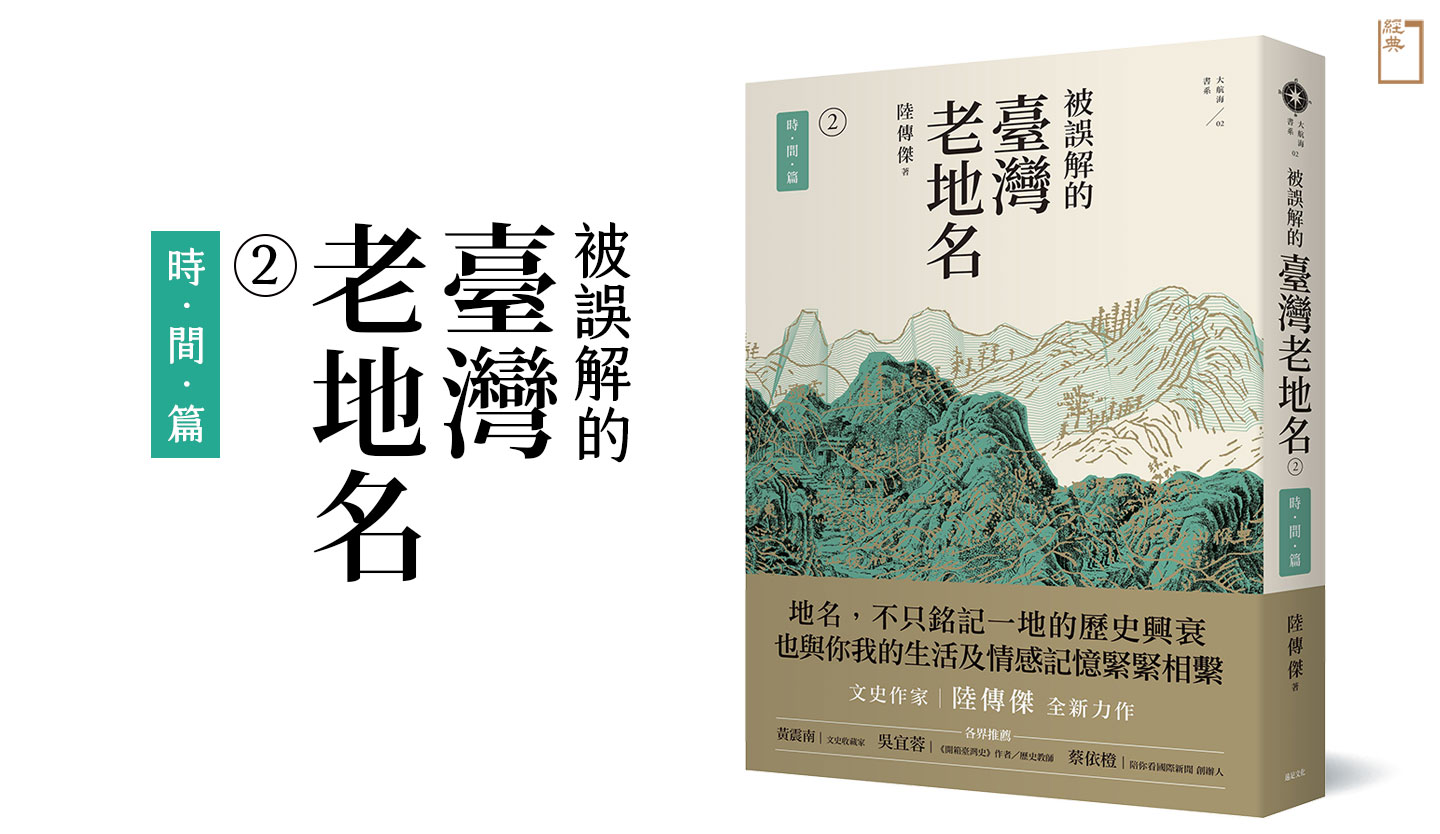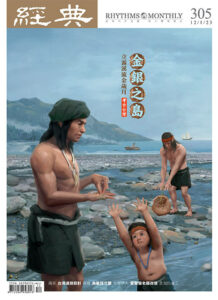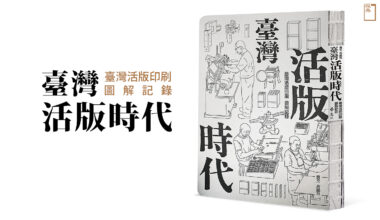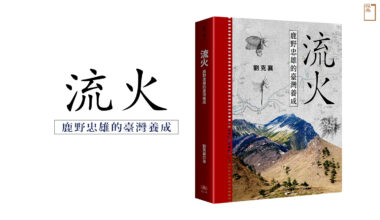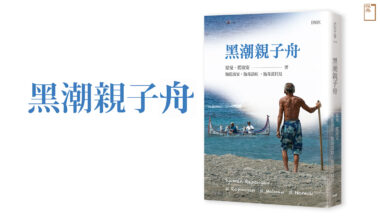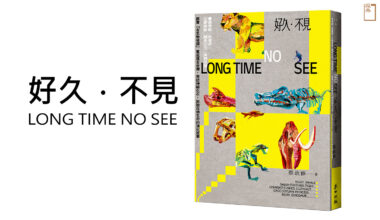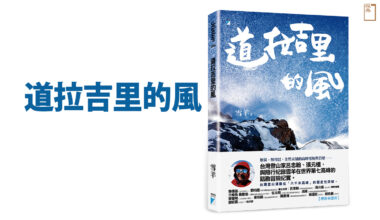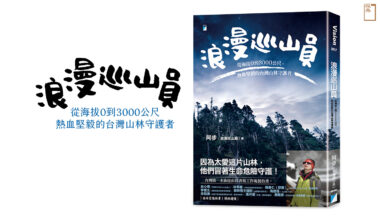大員、臺灣、埋冤?
臺灣之名源於「大員」,在臺灣已成為基本常識。一九六○年洪波浪與吳新榮編寫的《臺南縣志稿》在第三章第一節地名起源中提到:「臺灣社(Teyowan)今安平又書為『臺窩灣』,係當時一鯤鯓之地,明季陳第撰《東番記》所載之『大員』同一地,現在『臺灣』之名亦由此出。荷人建Zeelandia城(今之安平城)後原住平埔族被迫移徙新港及舊社(今之歸仁)」。
《臺南縣志稿》的作者短短幾句話,就將臺灣、大員的由來交代得清清楚楚。但長久以來我一直沒弄清楚大員、臺灣是如何從一個原住民聚落演變成全島的總名?學界也沒有這方面的專門研究(可能是我孤陋寡聞不得與聞),大家似乎認為這個問題想當然耳,沒必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但我認為,這是研究臺灣地名繞不過的坎,尤其「認同臺灣」在島內已是頭等大事,對臺灣之名的源由豈可怠慢!
這個問題困擾我多年,直到二○○五年前後我到蘇州的臺商工廠任職後,這個問題才有新的體會。
臺灣成為全島總名應是在荷蘭時代
當時臺商在華東地區最大的匯集處是以昆山富士康為核心的蘇州地區,臺商從事最多的是手機、筆記型電腦上下游供應鏈上的協力廠商。當時還沒有直航航班,蘇州的碩放機場以軍用為主,民用航班很少。臺商往來臺灣與蘇州之間,通常是從港澳轉機上海浦東機場,再驅車前往蘇州。那時我發現一個特別的現象,臺商之間往來問候基本上是「什麼時候回上海?」或「什麼時候去上海?」好像沒蘇州什麼事。明明他們工作的地點就在蘇州,卻很少提到,這是為什麼?難道是虛榮心使然? 好像沒那必要。
久而久之,我發現整個江南地區的臺商都有這種說法。後來我才發現只要轉機終點站是在上海的臺商,都有類似的說法。想通了這個問題,再反過來思考三、四百年前先民由大陸渡海來臺,抵達航船的終站——臺灣第一大商埠大員,就不難理解他們以「大員」稱呼整個臺灣島了。當然這是我個人的理解,要說明源由還得釐清「大員」到「臺灣」整個地名演變的脈絡。我認為「大員」、「臺灣」之所以成為臺灣島的總名,和大員從一個原住民小聚落發展成臺灣島上的第一大市鎮有關。
荷蘭時代初期商品交易並不在大員
一六二四年荷蘭人占領大員之後, 立即在港口附近營建熱蘭遮城(Zeelandia),但是商品交易活動並不在大員,而是在與大員隔著大港水道的北汕尾。當時的情況荷蘭人記錄得不多,但我們可以從一幅一六二六年西班牙人繪製的《福爾摩沙島上荷蘭人港口圖》窺見大員附近的地理人文訊息。
圖中的熱蘭遮城已經初見規模,荷蘭人的商館設在北汕尾的北端,挨著鹿耳門水道。北汕尾的南端畫了幾座小屋,圖上沒註明具體用途。我猜應該是中國商人的宿舍或貨棧。日本商館與荷蘭商館隔著鹿耳門水道設在北岸,顯然荷蘭人對日本人是很有戒心的。其實原因很簡單,當時荷蘭人最主要的貿易活動是將中國商品轉口到日本,如果日本人和中國人直接交易,那麼就沒荷蘭人什麼事了,而荷蘭人在此設商站、蓋城堡自然就白忙活一場了。
一六二九年大員市街初建,可能是未成規模,所以畫中的重點是擴建中的熱蘭遮城與荷蘭商館。當時的荷蘭商館建在大員市街與熱蘭遮城之間,商館旁有一座執行吊刑的木頭架。由此可見荷蘭已在此地建立司法管轄,商館應該是貿易、行政與司法的混合體。大員市街的建立是臺灣史上劃時代的一步,在地名學上的意義也是劃時代的一步。
如果荷蘭人將商館留在北汕尾或赤崁,大員就不會發展成一個商貿市街。那麼臺灣的總名也不會是現在大家習稱的「臺灣」,很可能是「北汕尾」或「赤崁」,或是發音類似的字眼。荷蘭方面,大員(Taioan)並非官方地名,官式地名是熱蘭遮(Zeelandia),不過荷蘭人在一般文書及地圖仍以大員(Taioan)稱之。
普特曼斯為大員的發展貢獻最大
「濱田彌兵衛事件」發生後奴易滋被解職,巴達維亞總部派普特曼斯(Hans Putmans)取代奴易滋擔任大員的第四任行政長官。普特曼斯在VOC殖民大員的歷史上是一位值得大書一筆的幹練官員。
普特曼斯看出中日轉口貿易是VOC在東亞最大的利益所在,為了消除「濱田彌兵衛事件」的惡劣影響,他派人赴日安撫德川幕府與薩摩藩,保住了VOC在平戶的商館。另一方面,普特曼斯與鄭芝龍放下了過去的恩恩怨怨,攜手合作打擊海盜勢力發展雙方貿易。兩手齊下的結果,大員的轉口貿易在一六三二年之後開始轉虧為盈。
除了轉口貿易之外,普特曼斯對大員商務最大的貢獻,應該是發掘了臺灣生產蔗糖的潛能。此後砂糖成為VOC在臺的重大利益。臺灣糖業的發展不僅為VOC創造了商機,同時也為臺灣漢人社會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在此背景下大員市街持續發展。普羅文西亞城(Provintia,今赤崁樓)也因中國農業移民的大增而發展成街市,但還是難以和大員相提並論。
大員市街的發展可以從普特曼斯主政時代繪製的地圖看出。比較知名的是一六三五年芬柏翁(Johannes Vingboons)繪製的《大員設計圖》和《熱蘭遮城景觀圖》。從這兩幅地圖可以清楚看出,隨著大員商務的發展,普特曼斯不但重新規畫大員市街,還營建了新的商館,並加強熱蘭遮城堡的防禦設施。比較令人費解的是,舊商館拆除後並沒在原地重建,而是併入熱蘭遮城。
之所以如此大概是因為一六三四年海盜劉香率領集團襲擊大員,為了安全只得將商館併入熱蘭遮城。
大員成為中國商人來臺目的地
一六三七年普特曼斯任滿返回VOC總公司述職時,曾向董事會展示了他的大員防禦與新市鎮的設計方案。董事會隨即下令巴達維亞總部必須根據普特曼斯的設計方案執行。普特曼斯的大員防禦新方案究竟是什麼模樣,如今已不復見,很可能和一六四四年《大員鳥瞰圖》呈現的景觀差不多。圖中的大員市街房舍儼然,鱗次櫛比,奠定了現今安平老街的風貌,成為當時臺灣最大,甚至是唯一的市鎮。
由於大員市街在荷蘭時代發展為臺灣第一大城鎮,中國商人赴臺基本上都是以大員為目的地,因此大員逐漸取代「小琉球」成為臺灣的總名。
荷蘭時代東印度公司雖然以Formosa為全島之名,但綜觀當時中國文獻除了大員,幾乎找不著福爾摩沙之名。可見荷蘭時代,大員不但是中國人對現今安平老街的稱呼,同時也逐漸發展為全臺灣島的總名。
明鄭驅走荷蘭人初期,仍以熱蘭遮城為軍政中心。鄭經主政之後將政經中心轉移到承天府(即荷蘭時代的普羅文西亞),大員改為安平鎮。民間傳說鄭氏因大員閩南語發音與「埋冤」相近,故厭惡之而改名。這個說法難以證明,不過從鄭氏部屬楊英所撰之《從征實錄》,可以了解明鄭時代大員、臺灣之名向安平過渡的歷程。
鄭氏占領大員之後將熱蘭遮城改稱為「臺灣城」,不久便又改名為「安平城」,以紀念鄭氏石井故里的安平城。楊英並沒有說明鄭氏是否因大員閩南語發音與「埋冤」相近才改名的,但單單是紀念鄭氏先人發跡之地,其實已經有相當充分的理由了。
事實上整個明鄭政權不單單是對大員,他們對所有由原住民語音譯的地名是完全不買帳的。鄭氏在承天府建立政權之後,從府、州、縣以下,以至坊里全改為「仁德」、「永康」、「新化」、「善化」、「歸仁」、「依仁」之類的八股式地名,原住民音譯地名一個不留。所以,與其說鄭氏厭惡大員閩南語發音與「埋冤」相近,還不如說厭惡所有音譯的原住民地名。
清政府早在拿下臺灣之前,就已經確定「臺灣」之名
臺灣之名最早出現清代官文書,我能查到的資料是康熙二年(一六六三)的《清實錄》,地圖則是康熙十三年(一六七四)南懷仁繪製的《坤輿全圖》。所以早在清政府將臺灣納入版圖的二十年前,就將臺灣島稱之為與「大員」同音的「臺灣」。當時明鄭治下臺灣總名為「東都」、「東寧」,清廷對明鄭一律以「偽」稱之,當然不可能承認「東都」、「東寧」,但又如何稱呼臺灣島?最實際的辦法當然是用民間習稱的「大員」。但大員字面上有高官之意,用來稱呼臺灣島,顯得有些不倫不類,所以與大員同音的「臺灣」應該是清政府比較能接受的地名稱呼。根據楊英《從征實錄》的記載,應該可以推論以「臺灣」取代「大員」是從明鄭投誠官兵那兒聽來的。
清政府將臺灣納入版圖之後,當然不可能沿用東寧、東都之名,不過除了承天府、天興縣和萬年縣之外,其他明鄭時代的地名全被清政府保留下來,連與鄭氏家族最直接關係的「安平城」都沒有被屏蔽,這不能不說清政府在地名政策上的寬大與包容。至於承天、天興和萬年之類關係到皇國帝祚,被替換掉也還算說得過去。有意思的是,清政府雖然承認「安平」取代「大員」,但卻頒給了「大員」更大的獎賞,即將「臺灣」連升三級正式成為臺灣島的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