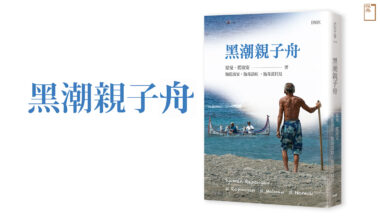我的無國界醫生夢
我是王伊蕾,一位婦產科醫師。
我大學就讀於國立陽明醫學院醫學系(一九八五年-一九九二年),陽明當時是僅次於台大醫科的第二志願。
學校於一九七四創建的時候,目的就是希望能培育醫師投入基礎醫療,解決偏鄉醫療資源不足的問題。剛開始陽明所有學生都是公費生,畢業後必須下鄉服務六年償還公費,才能拿回醫師證書。當時的聯考制度,丙組(醫農)考七科,國、英、數、物、化、生和三民主義。大家是以分數加總排名選校,沒有所謂的推甄跟加權計分,就是用總分硬碰硬來比拚。
台大、陽明、北醫分別是醫科的前三志願,但因為陽明畢業後需要下鄉服務,如果分數落在陽明的區間,很多不想下鄉的學生,就會直接選填別的醫學院。會選填陽明的學生,可能在心裡面都有畢業後要到偏鄉服務的自覺,和一顆服務人群的熱心。畢業後,也的確有許多同學就留在當初服務的地方繼續執業。
那時我們擁有的,只是滿滿的熱忱
學校中最大的社團是「勵青社」,是一個以服務社區為宗旨的社團。社團每年的重大活動,就是在暑假時下鄉服務,到群體醫療中心(就是衛生所)協助社區居民健康狀況訪查和衛教。
在我大四那年暑假,社團的服務隊來到雲林四湖。當時四湖群醫中心的主任徐永年醫師,就是陽明第一屆的學長(徐醫師目前擔任部立桃園醫院院長,當新冠疫情造成部桃院內感染時,正是徐院長臨危不亂,和疫情指揮中心合作控制疫情)。他下鄉到基層服務,對學弟妹們照顧有加,不但安排我們住進當地香客大樓,還幫我們借來一批腳踏車,讓我們能騎車前往各鄉鎮做家庭訪視。
還是醫學生的我們,有的只是滿滿的熱忱,和青澀粗淺的醫學知識,用極不輪轉的台語,向當地居民解釋著連我們自己都似懂非懂的疾病防治和慢性病控制的知識。而四湖的阿公阿嬤們一面剝著蚵殼、一面耐心聽著我們用破台語艱難地說明控制血壓、血糖的重要性,並不時用海口腔的台語和我們這群「肖年醫師」閒聊幾句。四湖土地貧脊、維生艱難,居民需要和大海搏鬥討生活,身體在大自然的嚴峻挑戰下,百病叢生。當阿公用帶著痰音的咳嗽,或阿嬤伸出變形的手指,問我們怎麼治才會好?還只是醫學生的我們,也只說得出些少抽菸、多休息的空泛言論來打發阿公阿嬤。內心則心虛地恨自己懂的是那麼少,能幫得上忙的地方是那麼微不足道,在病家前面,我們感覺自己就像煮過的蚵仔一樣,縮得好小好小。
每晚家訪回到住處,討論完當天的工作心得和隔天的計畫大綱後,大家就會圍坐成一圈,天南地北地聊天。當時就聽學長說有一個國際組織,專門派醫師前往戰亂的地區,為受到戰爭和天災傷害的民眾提供免費醫療,救死扶傷。當時我覺得這樣的醫生真了不起,比起什麼都不會、連台語都說得七零八落的自己,簡直是雲泥之別,心中也種下了無限的憧憬嚮往。
服務隊結束後回到學校,我翻找各種新聞報導資料,得知了「無國界醫生」(Médecins sans Frontières,簡稱MSF)這個組織。當時MSF主要是在戰亂頻仍的地區,為難民和流離失所的民眾提供醫療服務。看到穿著白背心的醫師戴著聽診器蹲在地上,為病重癱軟在地上的病人進行診療;或是替骨瘦如柴,因長期缺乏蛋白質而腹脹如鼓,連臉上爬滿蒼蠅都無力驅趕的小孩哺餵牛奶及營養品,更讓我對這個組織和工作人員產生了濃厚的敬佩之情。
一度與「無國界醫生」的夢想擦身而過
時光荏苒,七年醫學系畢業。服務六年的地點,我選擇在退輔會系統醫院完成,前四年留在台北榮民總醫院,後兩年下鄉服務。
擔任實習醫師時,我到婦產科產房見習自然生產,看到媽媽用盡力氣,滿頭大汗地吸氣,憋氣,用力,休息。吸氣,憋氣,用力,休息。一旁的醫護人員,也齊聲鼓勵產婦吸氣,憋氣,用力,休息。中間還穿插幫產婦擦汗、監聽胎兒心跳、準備生產器械、加溫新生兒照顧檯等工作。
魔鬼輪迴重複無數次後,胎兒終於探頭出來,隨著羊水胎脂平安誕生,用洪亮的哭聲宣告新生命的降臨與母親的辛苦告一段落。臉上交雜汗水與淚水的媽媽親吻著自己的寶貝,接生醫師則一面微笑看著這光景,一面熟練地拉出胎盤、按摩子宮、修補會陰,確保母體健康。目睹這一切的我不禁又感動又佩服,在畢業後即申請婦產科做為專科,進入台北榮總接受住院醫師訓練四年,取得婦產科專科醫師執照。接著又到竹東榮民醫院和桃園榮民醫院服務兩年。
在這六年期間,我依循著大多數女性的生命歷程,結婚、成為兩個女孩的媽媽。每天的日常生活被緊湊的臨床工作和柴米油鹽奶粉尿布塞得滿滿的,「無國界醫生」的夢只得愈飄愈遠……。
一九九九年,「無國界醫生」榮獲諾貝爾和平獎。那年我大女兒三歲,小女兒一歲,我也才剛服務期滿,在還完公費後到私人診所服務,努力在病患間建立口碑。聽到我憧憬的組織這麼厲害,我的心緒又開始飛揚……,但想到兩個上班前總拉著我不肯放的黏人幼兒,和還有二十年的房屋貸款,讓我飛揚的心直直摔回現實中。而且當時的MSF是以照顧戰爭中創傷的病患和落後地區感染熱帶傳染病的病患為主,需要的是外科系創傷急診和內科傳染病相關的專科醫師,在戰場邊要怎麼接生寶寶呢?這讓我的無國界醫生夢又再一次遠去。
後來,我開立了自己的診所。二十年前女醫師很少,女婦產科醫師更少,所以患者不少,診所的業務也穩定成長。當時患者意識抬頭,醫療糾紛時有所聞;而產科因為不可預期的合併症很多,產婦大多都是歡天喜地到醫院生產,如果結局不如預期,只要母子雙方有任何損傷,都唯接生醫師是問。婦產科醫師被告上法庭,或家屬到診所撒冥紙抗議的新聞屢見不鮮。評估的結果,我決定診所業務單純看診,不接生。雖然這讓我不用隨時on call,擔驚受怕,事業和家庭生活因此而獲得平衡,但沒有接生做產科,一直都是存在我心底的一個小小遺憾。
生命的脆弱,讓我體悟活在當下的重要
歲月如梭,轉眼兩個女兒長大成人,陸續上大學、出社會,有了自己的生活。診所工作穩定,但也一成不變。這時我已年屆五十,進入更年期:體力下滑、睡眠障礙、情緒低落。所有病人告訴我和書上寫的更年期症狀一一在自己身上應驗。雖然我有著人人稱羨的工作和生活,但總覺得好像少了什麼,想要突破瓶頸,嘗試不一樣的體驗。
一天,我在看診空檔吃飯上網的時候,忽然瞥見了「無國界醫生」徵求女性婦產科醫師的消息。原因是在阿富汗等伊斯蘭教國家,醫療資源不足,許多婦女必須冒著生命危險生產;然而民風保守,只接受女性婦產科醫師協助生產。這讓我的心跳瞬間漏了一拍──這,說的不就是我嗎?我心中怦然不已,恨不得馬上就報名加入;但開業多年,有許許多多信任我的病患、對診所向心力極強的員工,這數不盡的人情牽絆,不是說放下就可以放下的……,這讓我感到非常猶豫。
然而,行醫這行有好有壞,好處是可以幫助身邊的親朋好友,給出醫療建議;壞處是只要有朋友身體出狀況,做醫師的都是第一個知道。
在猶豫不決的這段期間,我有位大學同學,是一位成功的開業小兒科醫師,事業成功、家庭美滿,還曾邀我一起成立婦兒科聯合診所。他突然身體不適,入院檢查後發現是白血病(俗稱的血癌),開始一連串的化療、骨髓移植,同學們也從各處幫忙請託,希望他能獲得最好的治療;但每次在群組上看到他奮力抵抗病魔,身形日漸消瘦,我們心底都知道情況並不樂觀。
友人在健康檢查時意外發現大腸癌;同學的親戚罹患乳癌;一位熱愛運動,身體健康的學弟,在爬山到一半時心肌梗塞猝死。身邊共有十位左右的朋友不是意外罹病,就是英年早逝,讓我體悟生命的脆弱,與及時行善、活在當下的重要。
與其為逝者哀傷感嘆,不如在有生之年燃燒貢獻。幾經思考,在取得家人的支持後,我毅然決然暫時結束診所的營業,全心投入「無國界醫生」的人道救援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