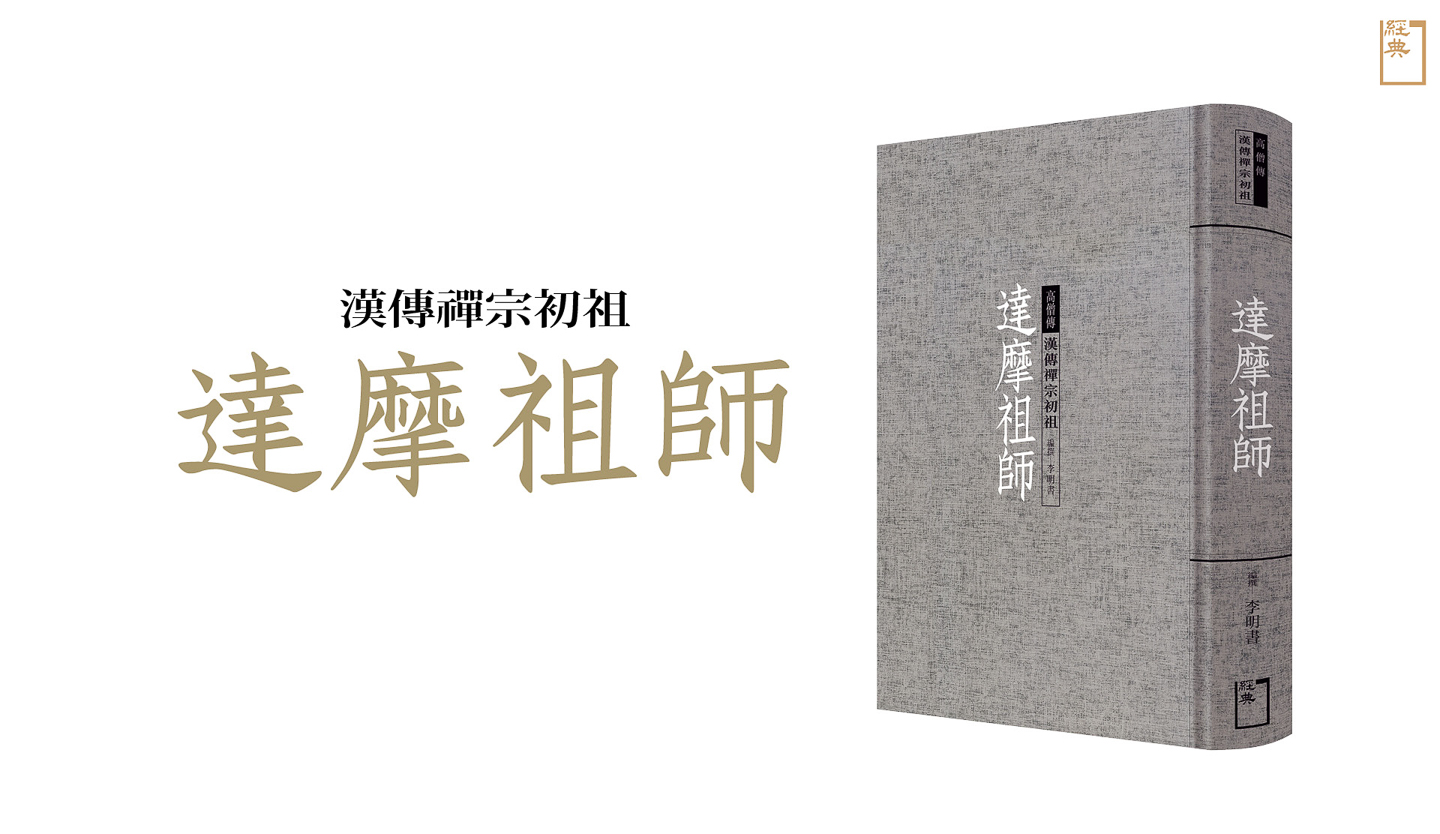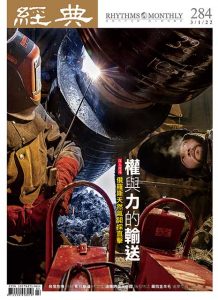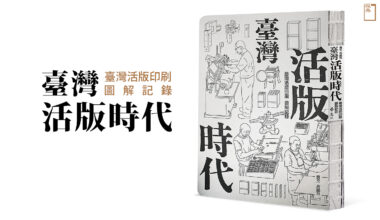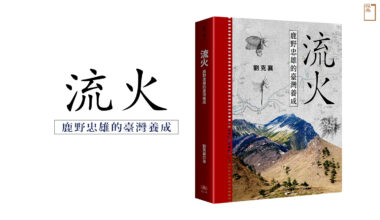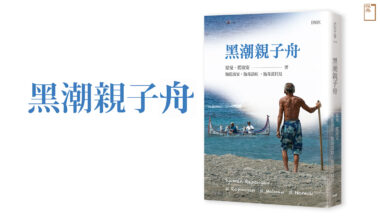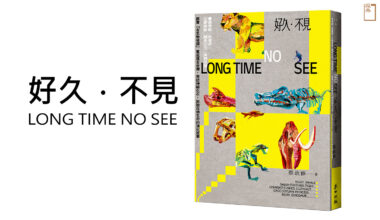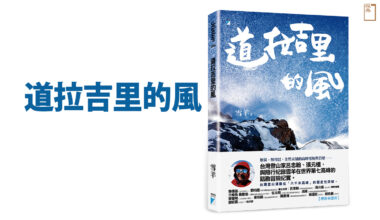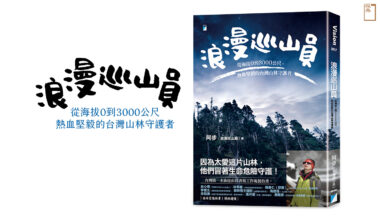香至國的三王子
神慧朗,聞皆曉悟。志存大乘,冥心虛寂;通微徹數,定學高之。
南天竺的香至國
在古代南天竺有個香至國,那是一個陽光普照、雨量充沛的美麗國度。香至國的國王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他用慈悲之心來治理國家,受到百姓的景仰與愛戴。香至王有三個兒子,分別是大王子月淨多羅、二王子功德多羅以及三王子菩提多羅。
三位王子氣質高貴且容貌俊美,性格卻不盡相同。大王子月淨多羅意氣風發,舉手投足豪邁矯健,英姿煥發;二王子功德多羅勇猛剛強,充滿霸氣與魄力,兩位王子都有著胸懷天下的入世情懷。和哥哥們不同,三王子菩提多羅是個眉目疏朗的沉靜少年,每當大哥、二哥慷慨激昂地與父王討論治國方針時,他總是靜靜站在一旁聆聽,極少參與討論,眼神時常流露悲憫目光。少年菩提多羅喜歡浸淫在王宮的藏經閣裡,往內在精神層面做深度的探求。
志存佛業的王子
根據《景德傳燈錄》記載,菩提達摩(梵名Bodhidharma)原名菩提多羅,後以西天二十七祖般若多羅為師,承法後改名「達摩」。祖師的原名、生卒年及原居地、種姓等資訊,在典籍中說法各有出入,其名稱在歷代亦有不同的寫法與揉和,例如: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與道宣的《續高僧傳》寫作「達摩」;《歷代法寶記》則作「菩提達摩多羅」;《曹溪大師別傳》記為「達摩多羅」;《寶林傳》寫為「菩提達磨」;而宋代以降的禪宗史書如《景德傳燈錄》、《傳法正宗記》等寫作「菩提達磨」。為了閱讀上的統一與方便,本書採用常見的寫法,作「達摩」;至於引用古籍史料或現代專著文章時,則保留原作者或典籍既有的用字。
曇林在〈略辨大乘入道四行及序〉中指出「法師者,西域南天竺國人,是大婆羅門國王第三子也」;道宣在《續高僧傳》也說其為「南天竺婆羅門種」;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則說達摩是「波斯國胡人」。至於香至國王子的身份,見於《祖堂集》、《景德傳燈錄》與《傳法正宗記》所載。學者屈大成則認為楊衒之應是將「波斯」與南天竺的「帕拉瓦」首都香至混淆。
少年菩提多羅天性高勝,有著異於常人的悟性及慈悲心。他聽說王宮百里外有位隱居修行的老法師佛陀跋陀,對於佛理和坐禪有著深刻的領悟,於是前往叩教,期待踏上學習佛法的道路。
與跋陀師父學解脫道
相傳菩提多羅王子最初是跟隨跋陀師父學習解脫道。每日天未破曉,便起身誦讀佛經,接著師父逐句講,不間斷地把握時間精進。跋陀法師除了講授佛典精義之外,更多時候皆是閉目坐禪,不分日夜,無懼寒暑。
所謂「解脫道」,字面的意思是指佛法所示,教人從煩惱中解脫的修行道路。進一步的內容,是指脫離貪、嗔、痴煩惱,出離六道輪迴之苦,從三界中超脫而出,達到「涅槃」的境界;這樣的修行者稱為「阿羅漢」。
在跋陀師父的指導下,菩提多羅王子凝志靜修,即便置身在酷暑濕熱的山林中,時時忍受蚊蚋橫行的侵擾,卻打亂不了王子的平穩安定。日子一天一天過去,菩提多羅無時不刻的用功。慢慢地,在一呼一吸之間安頓身心,摒除心中的妄念。
「除了坐禪,接下來還能做些什麼?」菩提多羅王子如是想。在美麗的香至國度裡,上達王宮貴族,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離不開生、老、病、死的煩惱,要如何幫助這些執迷的眾生?
正當思索之際,侍衛前來稟報:「般若多羅尊者到南天竺了!般若多羅尊者到南天竺了!」
般若多羅尊者是禪宗西天二十七代祖師,當香至國王得知尊者遊化而來,馬上禮請入宮,同時派人通知在山林裡修行的菩提多羅王子,盡速前往聆聽尊者開示。於是菩提多羅告別跋陀師父,起身回宮。
從「菩提多羅」到「菩提達摩」
既而尊者(般若多羅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
寶珠之辯
香至王許久沒見到小兒子菩提多羅,看著菩提多羅終於回到王宮,香至王藏不住心中滿滿的思念;眼眶泛淚地望著這個衣衫襤褸、清瘦的少年,他的外觀上全然沒有王子的華麗裝飾;香至王心想:「這孩子不知道受了多少苦!」但看菩提多羅眼神清澈如水,苦行的日子必定有某些覺悟及成長,國王只能暫忍不捨,喚人來替三王子沐浴梳洗,準備前往大殿聆聽般若多羅尊者說法。
這天,香至王宮裡擠得水泄不通,國王、貴族、僧侶、王公大臣,紛紛前來聽法。待眾人坐定後,香至王鄭重下令,拿出香至國中品質最好、最大的無價上品寶珠布施給般若多羅尊者,以表達供養之心。般若多羅尊者並不推辭,平靜地收下了這份貴重的禮物。只見流光溢彩的寶珠光彩奪目,王宮上上下下無一人不被吸引。
般若多羅尊者手持寶珠,走到王子們面前,緩緩地問道:「有什麼東西,能比這顆寶珠還要圓潤明亮的呢?」(「此珠圓明有能及此否?」)月淨多羅和功德多羅不約而同地說:「這顆寶珠無比珍貴,即便是金、銀、琉璃、珊瑚、琥珀、瑪瑙、硨磲等七寶,也無法超越它的貴重,只有尊者您的佛力和修為,才能與之匹配啊!」二位王子重申寶珠的無價,連帶對般若多羅尊者再次恭維。
菩提多羅有別於哥哥們回答迅速,先是靜靜站在一旁,待般若多羅尊者示意要他回答時,方才淡淡道出。《景德傳燈錄》生動地記載了這段充滿悟性的「寶珠之辯」:
第三子菩提多羅曰:「此是世寶,未足為上;於諸寶中,法寶為上。此是世光,未足為上;於諸光中,智光為上。此是世明,未足為上;於諸明中,心明為上。此珠光明,不能自照,要假智光。光辨於此;既辨此已,即知是珠;既知是珠,即明其寶。若明其寶,寶不自寶;若辨其珠,珠不自珠。珠不自珠者,要假智珠而辨世珠;寶不自寶,要假智寶以明法寶。然則師有其道,其寶即現;眾生有道,心寶亦然。」
菩提多羅的哥哥們只看到寶珠表面的光澤與世俗的價值,菩提多羅則認為寶珠只是世俗認為的寶貴之物(「世寶」);他進一步洞察到物質層面之上,比寶珠更可貴而不可限量的價值,那就是珍貴的「法寶」,也就是佛法的寶貴。菩提多羅接著用「世光」與「智光」、「世明」與「心明」對照,凸顯超越世俗光芒、明亮之上的,還有智慧的光芒與佛心(本心)的明亮。
由此可知,雖然般若多羅尊者手中的寶珠價值連城,但是持有的人如何看待寶珠,才能真正凸顯寶珠的價值;寶珠真正的光芒,並不是自己照耀而出的身,而是透過智慧的光芒去觀看才能散發出來;光芒散發出來之後,才能看出這是如何貴重的寶珠。同樣的道理,當我們用智慧、佛法去看寶珠時,寶珠就不再是世俗的凡物,而是能夠透顯智慧、佛法的寶物。只要人人都用合於佛法的正道去看這顆寶珠,這顆寶珠也就能夠成為映照佛心的寶物。
《五燈會元》中也有記載般若多羅尊者對王子們試珠的故事:「(般若多羅尊者)試令(菩提多羅)與二兄辨所施寶珠,發明心要。」由這段簡略的記載,可以看出尊者通過寶珠為喻來闡釋佛法,說明佛心的要旨。《五燈會元》中另有關於世尊向五方天王試珠的記載,故事和道理都非常相近,或可參照來看。同書卷一說:
世尊一日示隨色摩尼珠,問五方天王:「此珠而作何色?」時,五方天王互說異色。世尊復藏珠入袖,卻抬手曰:「此珠作何色?」天王曰:「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世尊嘆曰:「汝何迷倒之甚!吾將世珠示之,便各強說有青、黃、赤、白色;吾將真珠示之,便總不知。」時五方天王悉皆悟通。
書中記載,有一天,世尊拿出了一顆隨色摩尼珠,問在場的五方天王:「這顆寶珠是什麼顏色呢?」五方天王根據自己所見,回答各種不同的顏色。接著世尊把寶珠藏進袖子裡,然後舉手再問:「這顆寶珠是什麼顏色呢?」天王們看著世尊手上空無一物,不解地反問:「世尊您手中沒有東西呀!又哪有什麼顏色呢?」世尊聽到大家的回應後嘆了口氣,說道:「你們怎麼會如此顛倒錯亂呢?把世俗的寶珠給你們看,你們紛紛說有青色、黃色、紅色、白色等顏色;我把真正的寶珠拿給你們看,你們卻視而不見!」
直到此時,五方天王才真正悟通了佛法的深意。相傳摩尼寶珠「無有自色,乃隨所對物之色而現其色相」,其本身沒有色彩,會隨著對應角度不同,而顯現綻放青、黃、赤、白等不同色彩。天王們一開始只看到珠寶的種種色相,當世尊「藏珠」之後,天王們說:「佛手中無珠,何處有色?」落入了有、無的偏見中,正如《金剛經》所云:「凡所有相,皆是虛妄」,真正的空性,是無形無狀的。
對照菩提多羅所說的「心寶」,應與世尊所謂的「真珠」相應,都是清淨無雜質、空無一物的佛心、本心。
諸物三問
菩提多羅的回答使在場的眾人紛紛感到驚艷;因為他不看在事物的表面,充分透析般若智慧的深刻妙理,展現出不凡的悟性。般若多羅尊者亦「歎其辯慧」(《景德傳燈錄》),他接著問菩提多羅:
(般若多羅)乃復問曰:「於諸物中,何物無相?」
(菩提多羅)曰:「於諸物中,不起無相。」
(般若多羅)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高?」
(菩提多羅)曰:「於諸物中,人我最高。」
(般若多羅)又問:「於諸物中,何物最大?」
(菩提多羅)曰:「於諸物中,法性最大。」
般若多羅尊者提問什麼東西是「無相」、「最高」與「最大」?菩提多羅分別以「不起無相」、「人我最高」、「法性最大」回答。
所謂的「無」,不是什麼都沒有、什麼都不存在的虛無;「無相」是以空性、法性看待世間萬事萬物的差別相,不值取於是物的表象;但是「無相」本身也是一種相,所以必須連「無相」這個概念都不生起,才是真的認識到般若智慧。
「人我最高」旨在凸顯人身難得。雖然佛教重視三界六道的眾生,但是人是由下三道提升到上三道的關鍵,也是學習佛法因緣最為殊勝的階段。例如《雜阿含經》卷十五曾記載:
爾時,世尊告諸比丘:「譬如大地悉成大海,有一盲龜壽無量劫,百年一出其頭,海中有浮木,止有一孔,漂流海浪,隨風東西。盲龜百年一出其頭,當得遇此孔不?』……佛告阿難:『盲龜浮木,雖復差違,或復相得。愚癡凡夫漂流五趣,暫復人身,甚難於彼。」
在輪迴的過程中,轉生為人相比盲龜穿浮木孔的機率,更為微小渺茫,所以說「人我最高」。
最後提到「法性最大」,理由在於真正構成世間萬物的基本單位總稱為「法」;就算是再巨大的物品、價值再高的寶物,例如前面所說的寶珠,也不能脫離萬法而獨自存在,都可以拆解出無限的構成單位,所以說「法性最大」。
從「寶珠之辯」到上述的「三問」,般若多羅尊者旨在讓菩提多羅了解佛法的深意,不在於認知事物的表象,而是以智慧通達事物的根本,可以用佛法解開世間的萬事萬物。佛法所及,廣大而無邊際;其中的奧妙,還是在於個人心性的領會。
在一問一答之間,菩提多羅豁然開朗,般若多羅也為彼此相契而喜;通過問答以心印心,般若多羅知道這位小王子是值得堪負重任的大法器;然而,現下因緣尚未具足,尊者只能暫且將這份喜悅放在心裡,祕而不宣。依據《景德傳燈錄》記載:「尊者知是法嗣,以時尚未至,而默混之。」
捨位出家,改號「菩提達摩」
等待佛緣成熟的日子不知過了多久,歲月在轉瞬之間悄無聲息地流逝,直到香至王國身染重病,甚至出現雙手向空中抓攬的舉動。《傳法正宗記》中的敘事十分離奇:
其後,會父病既亟,輒以手覽空,雖左右不能止;菩提多羅因以問尊者曰:「吾父善興福,平若未有如其為心者;今感疾恍惚,手攬虛空,恐非善終,何其報之相反耶?我甚惑此;尊者果能釋之,願從出家。」
菩提多羅十分困惑:「為何父親病篤的時候,雙手朝著空中胡亂抓握,甚至隨侍左右的人協力阻止,也都沒辦法讓他停下來呢?」看到這樣的怪異情況,菩提多羅擔心父王將會不得善終。「一生勤政愛民又樂善好施的香至王,怎會落得如此下場?」「做那麼多善事,為何最後的果報是相反的呢?」帶著心中一個接連一個疑問的疑問,菩提多羅前去向般若多羅請教:「期待尊者能替我解答開示,我願意追隨您出家。」
般若多羅說:「這些都是業報之所反應出來的情況。世間眾人皆有業力果報,即使是三乘聖人也不例外;然而,業報的反應,有善業、惡業的區別。佛陀曾說:『人有為善之至,及其終也,報當生天,則天光下垂,如引經綵,欲其終者覽之,而神隨以上征。其光或五色互發者,蓋表其所嚮乃往天界也。』這就是說,如果你父王善報顯現,那麼在臨終的時候,將會看到天界的光降臨,如同彩布下垂,將會伸手攬取。所以這是善業的果報,表示他將往生天界,並不是不得善終。」不久後,香至王放下了躁動的雙手,安詳長眠。
香至王崩逝後,舉國上下悲淒不已。想起父王一生為了治國費盡心力,對兒子們養育栽培的劬勞,大王子月淨多羅和二王子功德多羅不禁放聲慟哭,不能自已。就在這個時候,他們看到菩提多羅穿越人群,靜靜地對著父親行禮,臉上沒有一絲哀容;禮畢後,菩提多羅閉上雙眼端然默坐,一動也不動。
「父親已經過世,我們再也見不到他了!菩提多羅一點也不難過嗎?他可是父王最疼愛的小兒子啊!怎麼會這麼無情呢!」月淨多羅和功德多羅不解弟弟的行徑,帶著既憤怒疑惑的心情,前去向般若多羅請教:「請問尊者,為何菩提多羅突然不言不語、坐定不起了?」般若多羅回答:「三王子現在正進入禪定的狀態,必將有所洞察,七天之後就會自行起身,請二位王子暫勿驚擾。」
雖然難解箇中緣由,但尊者都這樣說了,加上眼下以料理香至王的後事為要,月淨多羅和功德多羅也只能暫時先任由弟弟坐定不起。
七天後,菩提多羅打坐結束;他站起身來,告訴二位哥哥:「我在打坐的時候試圖觀看父親死後會到什麼地方去,只見那光明、無窮的太陽照耀著天地,沒有看到其他東西。」菩提多羅的看到的情景,和父王彌留時,般若多羅所述的內容相吻合;更為重要的是,七天七夜的打坐,更堅定了菩提多羅出家的決心。當初在山野之間追隨跋陀師父學習解脫道,除了坐禪之外,他不斷思索還能為眾生做些什麼;而今自己的父王崩逝,在眾人痛哭哀戚的悲嘆聲中,他知道自己的塵緣已盡。
因緣俱足後,菩提多羅和哥哥們告別,跟隨般若多羅出家。《傳法正宗記》記載菩提多羅如是對般若多羅說:「我素不顧國位,欲以法利物,然未得師,久有所待。今遇尊者,出家決矣!願慈悲見容。」從初見時的「寶珠之辯」,般若多羅早已知曉這位三王子是不可多得的法器;香至王崩逝後,菩提多羅又表明自己向來不眷戀王位;眼下時機已然成熟,便欣然接受其禮,為菩提多羅剃度。
《景德傳燈錄》記載了般若多羅為其改名的緣由:
既而,尊者謂曰:「汝於諸法已得通量。夫『達磨』者,通大之義也,宜名『達磨』。」因改號「菩提達磨」。
「達磨」(梵語 dharma)即為「法」的意思,或為一切法的總稱;在《景德傳燈錄》中解為「通大」,亦即通達萬事萬物的道理而廣大無邊際,也就是三問三答中的「法性最大」之意。般若多羅尊者認為菩提多羅通達佛法要理,所以將他的名字改為「菩提達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