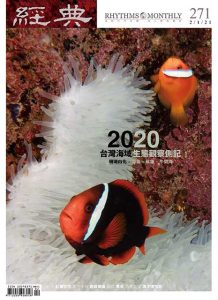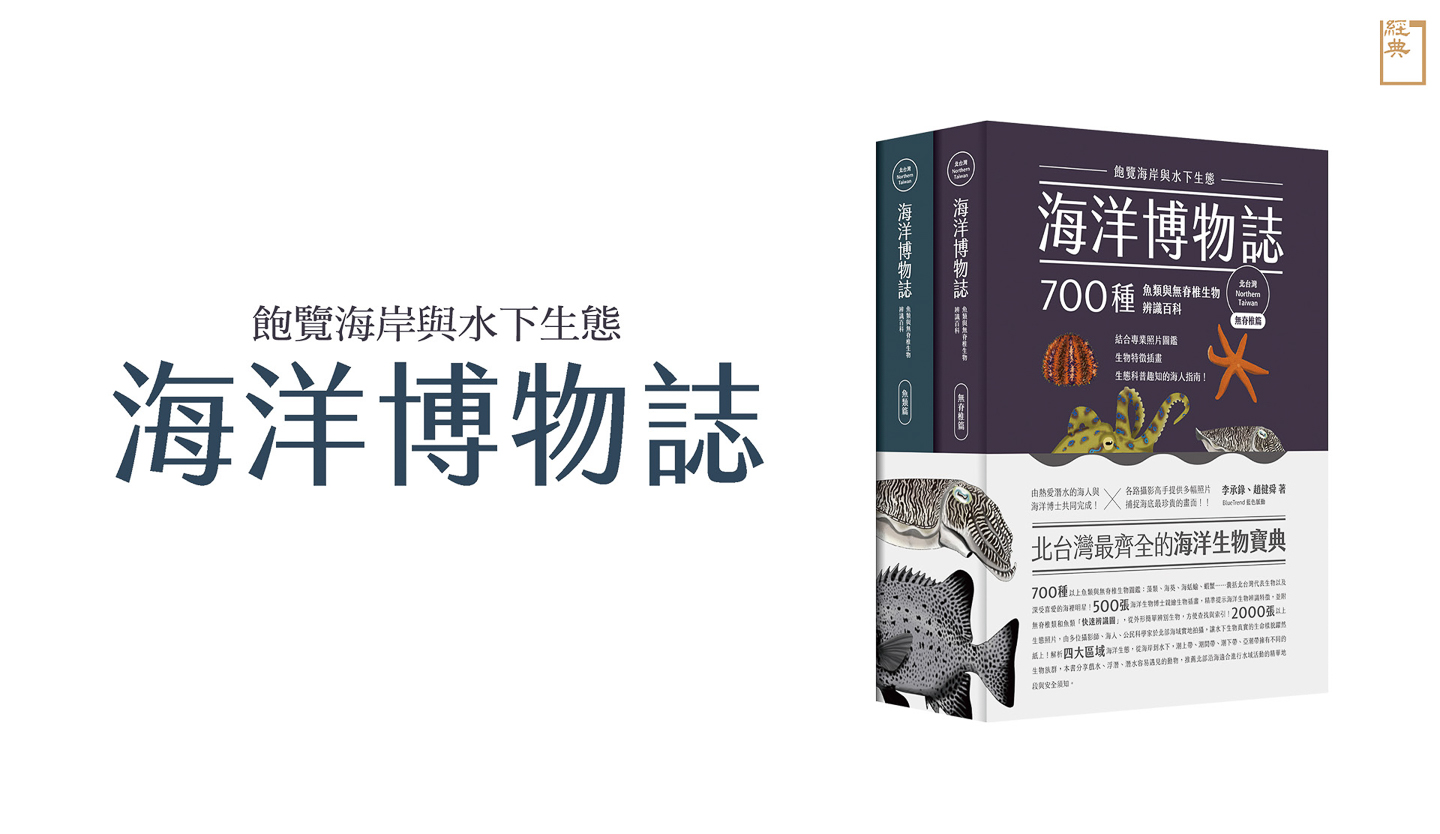你聽過「年獸」嗎?
沒等到對方回答,先是在筆記本上頓了一下,想了一會,在「破除迷信」、「解構神話」、「不必存在傳說」的現代觀念下,「年」這隻齜牙裂嘴的獸,是否還是讓人害怕?或者應該說「相信害怕」?舊年尾、新年頭,台灣冬季的凍寒嚴冷,唯恐生存挑戰的披荊斬棘、籌措無門的貧瘠環境,「過得了」與「過不了」的心境,「難過」總是「能過」的躁動不安,在現今,還能體會得到嗎?
對抗與戰勝,絕望與希望,過與不過,你聽過年獸嗎?
眼前台灣觀光地方創生協會秘書長施景耀,在一聽到問題後,旋即將回憶拉到就讀小學時,國立編譯館出版國語課本裡的一篇課文〈年獸來了〉,他笑著說:「那是我第一次學『獸』字,筆畫多,印象深刻,因此,年獸也深刻地成為我對過年的基礎認識。」從事歷史街區導覽,同時在地教育推廣專員的張教煌則是談到小時讀過一整套的《漢聲中國童話》,十二個月的精裝書,一月的書皮是大紅色的,歡騰喜慶,那隻怕紅色、怕鞭炮的年獸就在裡頭,但長大了一點,他卻發現:「明明農曆過年大概是國曆的二月,怎麼會是屬於《一月的故事》裡?」
這似乎點出了一個問題:元旦、正月初一,台灣竟然擁有兩個「年」。
三個時間軸,兩個迎年,一個台灣
倒數:三、二、一、○……當數字跳動逐漸歸零,或是秒針的的的指往十二,精準而尖銳地刺向氣球般,一下子爆破出群體狂歡的氛圍,台上最壓軸的巨星表演即將登場,新的一年開始,時間再從倒數轉為正數:一、二、三、四、五……台北一○一跨年煙火表演時間年年加長,Happy new year,日新又新,還要求變,送往、迎來,才到二○二一年而已,不久的歲次庚子到辛丑,則是另一道年關了。
「新年快樂」等於具備了兩種意涵。
台灣現行紀年有天干地支紀年、西元紀年、民國紀年,彷彿如同三個時間軸般,持續載錄台灣的歷史;新曆與舊曆,則是讓台灣迎來兩次的「新年」。
「新年」也是兩種面貌。一個稱「跨年」,一個叫「過年」。
因此,「新年」在詞彙上,也有兩種文化意義:元旦與初一、Happy new year與恭喜發財、大型派對與民俗節慶、現代進步與傳統守舊,城市與鄉村、知識分子與庶民百姓、青年與長輩,甚至是國語與台語。
中研院台灣史研究所研究專員林玉茹的研究中指出,關鍵點在日治時期。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採用現代化的新曆,一八九五年,隨日本統治台灣引進,新的元旦過年模式開始影響台灣,制度面以教育、政策,並透過讓台灣人參與元旦前後的活動,逐步讓日本文化思維融入台灣,甚者在一九三七年中日戰爭爆發,「皇民化」企圖將台灣打造為「真正的日本人」,其中「廢舊正」,施行舊曆年禁令,取消放假,企圖讓舊曆過年的意義消失。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退出台灣,中華民國政府接管後,「去日本化」的種種舉措,讓本來地下化、隱形化的舊曆過年得以延續下去。
有趣的是,新曆並未因此消失,因應全球化趨勢,並在資本商業操作的運籌帷幄中,還有政治考量下,不同政權日子底下的文化,是交錯而嫁接的存在。兩度迎接新年,概念各自獨立又相互挪用,在台灣的當代,習以為常。
就像二○二一年的跨年,台南中西區聯合九間宮廟,凸顯獨特的宮廟文化,舉辦「作伙來敲鐘」活動,以一百○八聲鐘鳴的祈願儀式,深沉鐘聲響,祝福民眾萬般煩惱輕。在全台各地舉辦跨年晚會、煙火施放的同時,將傳統交融於現代。
而舊曆過年經過不同特質的政權文化,在地化、時代演進而改變,這唯一的台灣因而多元紛呈。
除了年獸的故事
但是,怎麼看「年」字,都不像是一隻獸該有的可怕稱呼。
甲骨文裡的「年」,上「禾」下「人」,如人背穀物,是穀稷豐熟之意,所以,「穀稷豐熟」是隻怪獸,也有人說,是道關卡,冷峻冬日飢餓難挨,年來了,路有凍死骨,是窘困環境的化想,同時「穀稷豐熟」也是這段時間的期望。而耕研居宗教民俗研究室主持人謝宗榮則以節氣變化來解釋:「所謂年獸的本質其實就是陽曆歲末,『陰氣』變形的具象化形象。」
民俗亂彈執行編輯溫宗翰卻談到年獸的故事是「戰後官方民族主義宣染影響」,台中教育大學副教授林茂賢也提出「國」不同,「風」也不同,「俗」必相異。有異於眾熟知的年獸故事,台灣的過年起源有另一個「沉地傳說」。
相傳,神桌上的燈猴(燭台)終年掌燈照明,卻未曾受到台灣人民的感恩祭祀,一狀告向玉皇上帝,玉旨以「除夕午夜台灣島沉」為懲下達,經由土地公(有另一說法是灶君)告知,並委由觀世音菩薩求情勸阻。然而台灣百姓在得知後,先是在除夕沉島前,將家中供奉的神明送回天庭,免受牽連。待除夕,祭祖告別,夜時,與家人共進「最後的晚餐」,在吃飽喝足後,取出錢財共分,一同守夜。卻不想,島未沉,到初一天明,安然度過,台灣百姓莫不互道恭喜,至廟祭拜,感謝上蒼、觀世音菩薩庇佑。但恐懼仍未消,初二,出嫁女兒返回娘家探視,再次確認父母親友是否平安。要到初四,確認危機真的解除,才將諸神迎回家中。初五恢復正常後,初六農耕依舊,扛起鋤頭、挑肥灌溉,恢復尋常農業作息。
「沉地傳說」當中,豐富想像力的穿針引線,細細縫合台灣景狀:有潑辣頑皮、與人索求的「猴」,想來應該是台灣獼猴,就像高雄壽山上向登山客伸手奪取,還是開窗闖進高雄中山大學的學生宿舍,翻找食物大鬧一番,這是對於自然生物的體認。還有「台灣島」還會「沉」,地震的可怖感受恐怕不是現在才有,長久以來是居住災害的挑戰。島嶼上主要是「農耕」。還有「回娘家」所彰顯出來的父系社會。以及和「神」生活,將神聖視為一種家常,同時也以神聖來反省與檢討、總結與重算,過年習俗在「沉地傳說」裡嶄露無遺。
溫宗翰寫到:「過年傳說表現著農業社會時期,漢人面對台灣生活空間的體認,也涉及漢人移民在此落地生根以後,對此地產生了何種新的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