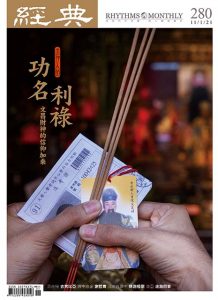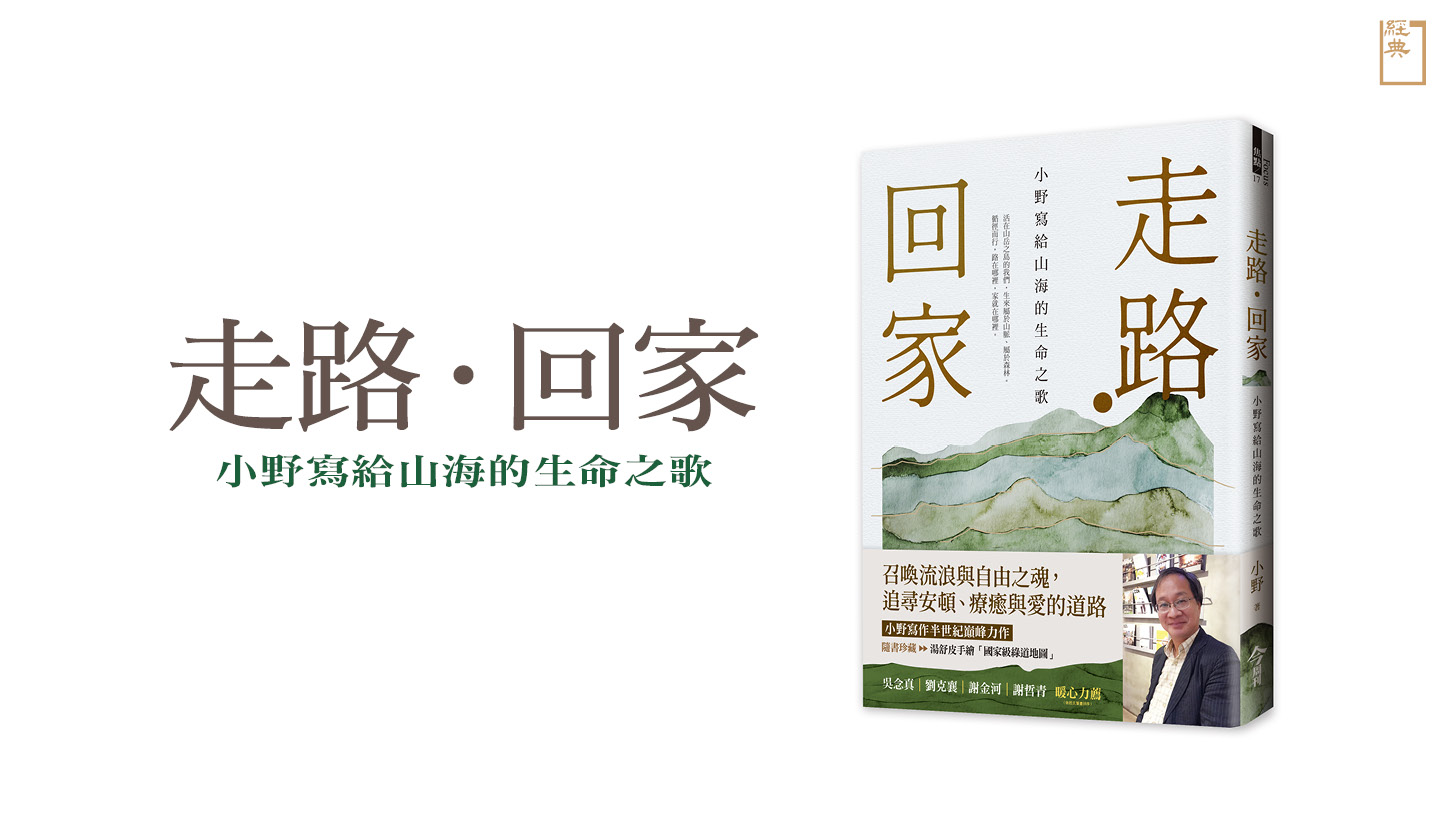高雄市文武聖殿三樓外,懸掛一片琳琅滿目的祈福卡,有的寫得無一留白,有的寫得簡潔有力,也有語氣是從容的十足把握,以及暗藏心胸的殷切期盼。
一時看過去,彷彿他們正將心中的「理想」喊得振振有聲,充滿希望——各個院校系所的學子志願外,還有許多出社會後各式的證照、檢定、升遷等——無論個人志向的功名實踐,還是職涯發展的利祿晉升,台灣民間信仰所面對的「求取」,無疑顯示每個人勇敢在社會環境裡,追求自我價值的直接兌現,為了更好的人生。
個人的識字到地方的文教
一定不少人自小聽過種種「用功讀書」的苦口婆心。對於書本傳遞知識的重視,但凡書頁有字,長輩必定會告誡:「袂使拆破字紙。」就連餐桌上都有「小孩子不可以吃雞爪,不然很會撕字紙」的穿鑿附會,長輩們的禁止,透過尊重珍惜聖賢之字,來提醒讀冊人需有嚴謹的學習態度,也反映早期台灣教育的不普及,識字作為學問基礎、權力象徵的崇尚心態。
然而,在「讀聖賢書,所為何事」的思考下,文以載「道」的意涵,指在學問(說)之外,更重視學子的內在涵養、人格養成,以作為立身處世的道路指引。
也因此,「文教」被視為地方發展的文明指標,早期台灣各地以「倡勵文教」為目的,民間建有「書院」來彌補官學的不足,除了構築傳遞學問的教育空間,同時健全地方教化體制,而書院內,皆奉祀文昌信仰之神祇。
如一八八七年(清光緒十三年)台中大肚由地方仕紳鳩資創建「磺溪書院」,教授漢學,內設有「文昌祠」供奉五文昌(文昌帝君、魁斗星君、文衡帝君、孚佑帝君、朱衣星君),為地方文教發展的中心,是現今台中大肚國小的前身。
自台中大肚國小退休的主任王政綱分享,每年農曆二月初三文昌帝君聖誕時,大肚國小的師生皆會前來祝壽,以示教育裡最為重要的「果子,拜樹頭;飲泉水,思源頭」。也因為這樣「不忘本」的緣由,讓王政綱開始投入磺溪書院的研究。
王政綱說:「一座古蹟不僅是歷史溯源的回顧,磺溪書院的建築形式、裝飾藝術、空間規畫,將尊卑、長幼、男女等觀念,以及教學裡的尊師重道等倫理道德,甚至是對學子的祝福與期許,具體而微地實現在這個教育環境裡。」
有別於以神祇為主體所延伸出來的廟宇空間,書院以教育空間為主體,將文昌信仰如同以「百年樹人」的精神,種植進入書院,茁壯地方的教育,讓「文昌祠」除了祈願、祝禱、看顧學子等信仰意義外,藉由星宿命運、傳說典故中的聖賢榜樣,在「有為者亦若是」的崇拜激勵下,建構一套祈福祝願、典範精神、倫理觀念的士人思維,讓供奉文昌神祇也成為提倡文教之一環。
除了追尋學問與涵養內在,受隋代以降科舉制度的發展影響,學識藉由「考試」,一個較為公平的機會,以突破原生階級囿限,轉換成「光耀門楣」的世俗實質價值。
考試文化下的文運昌盛
不論是人才選拔的「官位仕途」,還是教育體制的「學位前程」,由讀書打造的錦繡未來,一路上,互為表裡的「考試」如同一道道的關卡,能過或不能,又或者一再撞牆的掙扎,甚至耗費心力的拐彎繞路,隨著台灣的教育普及化,逐漸成為每一個人在學習歷程的必經心路。
同時,也存在著最大的變因,面對考試「既未知卻又決定未來」的徬徨,以及具有相當程度的優劣競爭壓力等,反映在文昌信仰,台灣各地廟宇普遍旁祀文昌帝君,特別講究當中對於「讀書具備,尚欠考運」的祈求,參拜學生除了祭品,大都準備「准考證影本」,放置文昌帝君神前,除了載錄考生資料外,清楚明白的考試資訊(號碼、科目、日期、時間、試場等)更將祈願設定在現場應試的順遂。
高雄市文武聖殿總幹事朱威亮說:「三樓大成殿供奉大成至聖先師(孔子)、大魁夫子(魁星)、文昌帝君,一年辦理至少四次的考生祈福活動。」配合當年度的大考考期,或有增加場次,在傳統聖誕慶典之餘,成為回應台灣現代教育體制的年例活動。
近年,期許學子的轉變,台南市政府文化局局長葉澤山強調:「多元適性的教育方針,多元的升學管道讓學生不再以『第一志願』為目標。」由各種考試所實踐的個人志向,祈求內容因而紛呈,「狀元」一詞,不再只限於「士」的頂尖地位,也在於追求各工百業的理想人生。
正因為「考試功名」在現代生活仍是求學必經,舉辦第四年的「赤崁祭魁星」,於農曆七月初七魁星爺聖誕,在黃昏時刻率領學子祭祀。同時,以魁星爺為亮點,探討神像形態,關注教育趨勢、考生心理,並介紹祭祀供品的諧音寓意,多是求學的期望與提醒,乃至藉由考試文化的古今連結,開發文創商品,葉澤山說:「透過『祭魁星』,目的是回溯『蓬壺書院』的文教發展,以及『赤崁樓』的歷史脈絡,形成走進古蹟的契機。」
這也表示,台灣民間信仰的神祇,可以是歷史回顧的媒介,也是人文需求的關懷。就像在赤崁樓文昌閣二樓坐鎮的魁星爺,腳踢斗、持珠筆的「魁星點狀元」,踏鰲魚的「獨占鰲頭」,星宿化身為神形,由「奎」字轉為「魁」字,如有鬼貌,卻蘊涵多少欲爭得功名「首」意的寄望,自蓬壺書院至今,擲筊在木構建物的地板上特別大聲,像魁星爺用力回應著古往今來的學子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