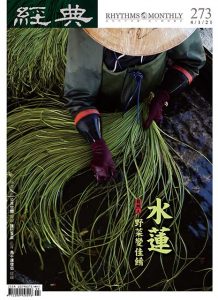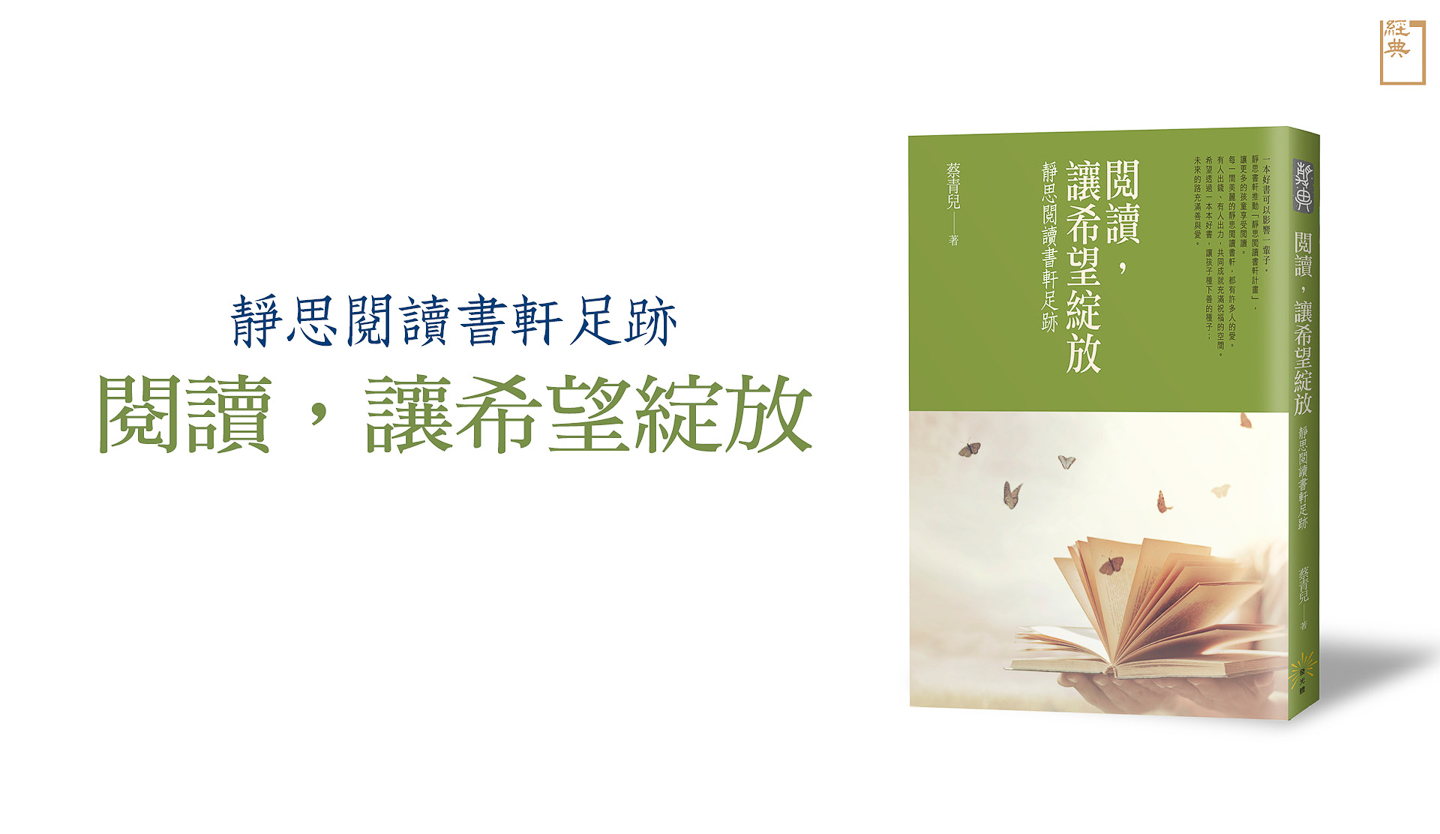退駕。
硬生生地抽離力量,全身癱軟。就像原本壟罩在身上的強大低氣壓,對流旺盛,有烏雲、有豪雨、有霹靂如電、有狂暴如風,他如此形容,一下子煙消雲散,天氣清朗。還要一段時間恢復,身上血痕還未乾,猶有汗水。筆生備妥毛巾與上衣,叫了幾聲他的名字。旁人架扶,老一輩教到,從褲頭將他提起來,背後左右肩胛骨各拍一下,劍指點向龍骨(脊椎),順勢劃下。
他悠悠醒來,像從遠方歸來。
想起前不久他們的玩笑話:「來者何神?」台語詢問起來倒變成了肯定句:「來吃胡蠅!」一句是問神報行頭,另一句是架構在問神的基礎上,諧音的趣味,關於人的戲謔。
恍惚之間,是神、是人,宛如當下是一幕劇情的切換,有神聖嚴肅,也有嘻笑怒罵。
「身」為一位信仰
這一幕則是先端放上一只空茶杯,釉色勻潤,看來是以茶水養浸多日,用在此時,他再斟上剛烹好的茶,觀茶湯、聞茶香,這種畫面在廟宇空間裡屢見不鮮,但對照面前的他,卻有不合時宜的老成。若說斜槓是現代人的時代特徵,那麼陳浩銓在介紹上一定是「展場設計師」/「淡水玄真宮乩身」。這兩種迥異的場域邏輯在陳浩銓的言談中跳躍,有些違和,一開始難以連結,好像路上幾處小坑,走過去不免停下腳步來,一再詢問「為什麼」。
年僅二十七歲而已,熟練地燒水泡茶,一邊說起工作歷程、職場甘苦,與時下年輕人並無不同,深褐色的頭髮燙捲得有型,上班工作、下班人生,只是自小就勤跑廟宇。為什麼當乩身?他舉了動漫《數碼寶貝》裡的橋段,說是「天選之人」。恰巧有信徒前來年前問事,從詢問內容裡熟稔地判別輕重緩急,為其仔細解說步驟,先以求得允筊為首要,在不影響工作為原則,年前有哪幾日他可以,態度不因年紀與身分而卑亢,這種跳躍在他的身上其實銜接得並不衝突。
陳浩銓說:「傳統乩身作為斜槓後的一種身分,是相當普遍的現象。」
五寶與「血」
五寶,視作五種武裝力量,神明統御「五營」的象徵,在展現神威的同時,作用於發兵與安營。而操演五寶所流的「血」,在民俗觀念裡,是人的精、氣、神,「紅」的色澤具驅邪避煞的暗示,透過顏色與儀式具體而微地呈現出一種靈力的象徵。
在現代,從這種身分的義務逐漸發展到成為職業,到表演性質的儀式操演,甚至是一種「角色」,變成認識乩身的多種視窗。近年不乏有影視作品,如電影《紅衣小女孩》系列;電視劇《花甲男孩轉大人》、《通靈少女》等,有寫實地貫穿在情節線裡,完整人物形象的具體性格,也有奇幻地利用神魔元素的戲劇張力,對於未知世界的想像與探索鋪展為劇情主軸,題材的特殊成為引人入勝的關鍵,畢竟,在講究實證的科學思潮、日新月異的科技,相信用「已知」來逐步定義「未知」的趨勢下,乩身文化在現代社會裡逐漸演進為一種「知道」,但不求甚解,一方面是對於神祕的未知,另一方面,台南聚宋宮前文宣組組長郭柏川說:「太多是迷信,太少則像是為了舞弄而舞弄。」過於現實與超現實,總叫人疑神也疑鬼。
然而,這會有個釜底抽薪的問題:為什麼需要「乩身」這樣一個神職?
耕研居宗教民俗研究室主持人謝宗榮將「乩」字拆解──占、乚,說明乩身源於占卜文化。人(巫覡)使用法器(武器),在面對生存挑戰以卜筮吉凶,祈禱之外,試圖尋求溝通,以探知神鬼意,現代常見的擲筊、抽籤等皆屬於占卜文化的一環。更進一步的,神降於人(巫覡)為「乩」以告訴,讓溝通更為直接。人有求,由於神對於「形」的限制,因此附於(或藉由)「人」的肉身來示現,具備神的架勢及動作,或寫,或吟唱,或開口說話,有官話、國語、台語,甚至是以「天語」來回應。
為台灣民間信仰的「媒介」之一,廟宇香火鼎盛的招牌、儀式的主持引導,甚至是地方公共事務的凝聚與號召等,乩身除了是神的代言人,更沉負著社會責任,讓神以另一種型態融入常民生活中,而乩身因為「雙重身分」在信仰社群、地方社會裡的具有一定分量。
一九八○、一九九○年代大家樂、六合彩等「明牌」風潮,透過乩身文化裡的雙向溝通──信眾疑難雜症的人生百「問」,與乩身靈驗無比的神奇解「答」──問明牌、逼號碼,趨之若鶩的信仰景象,橫財致富、傾家蕩產的警世,成為台灣賭博經濟時代的記憶。
除此之外,讓神明的形象性格,如王爺的威嚴兇惡、太子的頑皮純真、濟公的笑談隨和等,鮮明而獨特地展現,在南投名間鄉蹲點十多年,投入研究傳統乩身文化的溫宗翰則是認為,神明透過乩身與信仰場域的社群互動,性格的展現更是人對於「成聖典範」的投射。
陳浩銓強調:「但我是人。」南投松柏嶺受天宮筆生李澍慶則分享道,常年在旁協助乩身處理大小事,也會被信眾詢問對於神的認知是否與一般人不一樣?「沒有什麼不一樣,神還是神。」
面對這種既切割,又相關的人神關係,新北龍鳳玄太宮乩身李祖虎則談到,降駕過程,常有十分靈、七分靈、三分靈的說法,表示神降駕附身時的輕重影響著人的意識,這樣「以人的視角看神,以神的態度看人」的狀態,透過雙重視角的切換,「學到最重要的是『禮』。」李祖虎說,辦事過程指示爐下弟子的句子,皆以「請」字為開頭,叮嚀告誡再三,恪守傳統禮節。西拉雅族的尪姨尤威仁則是受阿立祖交代:「要去幫助那些『袂使講話的人』。」因此尤威仁全心投入殯葬業,業務之餘,收留無主枯骨,斜槓的兩端各是度生、度死。台南普濟殿總幹事洪忠義,人稱「師兄」,對於耳通(靈通的一種,指神藉由人的耳朵傳遞話語)的開啟只簡單說一句「時間到了」,「吾」是他首次聽到池府王爺說的第一個字,印象最深是有次隨池府王爺到外地救得一人,後來聽聞那個人為地方惡霸,有人質疑,為什麼要救他?就連洪忠義本人也質問這件事的正確性,而池府王爺只是說:「弟子再惡,吾救感化。」
成為乩身:神的降駕,人的言行
走進七、八坪的空間裡,兩張單人床,一張神桌、一張書桌,後來隔有一間廁所,若沒有大片紅紙將窗戶黏遮得密實,僅留上方抽風機讓空氣得以流通,就連門口也用一塊大紅布遮蓋,很像是等待出租的學生宿舍──這裡是南投松柏嶺受天宮的受禁房。
說是學生宿舍其實很貼切,「傳統乩身」的生成條件,南投松柏嶺受天宮乩身陳建宇表示,由天、地、人三者組成,必須經過睽睽眾目,在公開的慶典或儀式裡,由神明採乩,也就是首次「起駕」,這是「天」的部分。取得「天選之人」的公信度後,再向祖先擲筊(稱為「辭祖先」),獲同意三允筊,這是「地」的部分。同時,父母也需要同意,畢竟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乩身未來若有損傷,需先探問父母意願。接著「坐禁」,看定好日子,由老乩身帶領,進入受禁房閉關。陳建宇分享道,何時出關當下其實不知,這裡最多可到十二天,在受禁房內由神明降駕指示出關時間。他指了指窗,說與筆生李澍慶在一同受禁期間,頑皮地黏上一張紅紙,製作成可以翻閱的方式,寫下一篇受禁守則:「老鳥有交代,叫你要忍耐,時間到了自然出去。」忍耐什麼?受禁房內,僅能吃水果,也不能夠上大號、不能洗澡,裡頭沒有手機、沒有時鐘。過程強調的「清淨」,是淨爐二十四小時檀煙不斷,是完全地與世隔絕,顛覆了人的日常,成為乩身的非常。「睡覺、睡覺,還是睡覺。」他笑著說。除了睡眠,就是與李澍慶談天說地,對於時間的感受,「在睡與醒之間,就是上頭抽風機的扇片縫隙,看出去是白天還是晚上。」
這樣的禁,陳浩銓說:「門的『鎖』是在房內,開與不開,在於自己的心。」受禁七日的他坦言,前兩天極度焦躁,幾度要奪門而出,耐住性子與靜下心來,是他在受禁房學到的課題。
出受禁房之時,也須由老乩身(或者由法師)領出,這並不代表從此就是一位乩身。溫宗翰表示:「傳統乩身的生成就是完成一趟『公共化』的過程,由信仰社群來成就。」自採乩、辭祖先、問父母、受禁,到「訓乩」,由老乩身(或法師)檢驗,訓練腳步、手路、傳授操練五寶,就是一位本身經過公共認定、具有信仰社群話語權的人,在轉移「公共身分」給予新乩身。
同時,這也顯示出,「傳統乩身的公共性質,也促使乩身必須講究品德與修為,才能維持大眾的認同。」溫宗翰說道。因此,成為乩身之後,警惕自身、努力修為,獲得大眾的認同,反而是最為重要的事。台南集福宮乩身吳燦耀則提到成為乩身之路上,除了神明的考驗,信仰社群也會不斷地「試」,包含靈驗,更有對於一言一行的品格,與公共事務執行的能力。這也是天、地、人所組成的傳統乩身條件裡,最後「人」的部分,最是長路漫漫的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