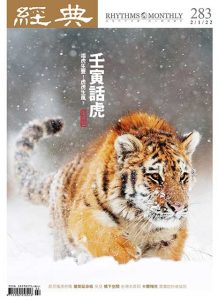英國「湖畔詩人」華茲華斯(一七七○年—一八五○年)的詩作《早春》這樣的寫著:
我躺臥在樹林之中,
聽著融諧的千萬聲音,
閑適的情緒,愉快的思想,
卻帶來了憂心忡忡。
大自然把她的美好事物,
通過我聯繫人的靈魂,
而我痛心萬分,想起了
人怎樣對待著人。
那邊綠蔭中的櫻草花叢,
有長春花在把花園編織,
我深信每朵花不論大小,
都能享受它呼吸的空氣。
四周的鳥兒跳了又耍,
我不知道它們想些什麼,
但它們每個細微的動作,
似乎都激起心頭的歡樂。
萌芽的嫩枝張臂如扇,
捕捉那陣陣的清風,
使我沒法不深切地感到,
它們也自有歡欣。
如果上天叫我這樣相信,
如果這是大自然的用心,
難道我沒有理由悲嘆,
人怎樣對待著人?
在華茲華斯的眼裡,大自然時時釋放著美善,讓人可以在谿壑水邊漫步徜徉,在林蔭底下閒緻臥躺;可以任由清風拂面;可以欣賞樹梢的互訪;可以聆聽鳥叫蟲鳴。色彩編織的花叢,翩翩飛舞的蝶影,湖光瀲灩,挽人流連。抽枝萌葉,張臂如扇,迎抱皎月翠山。風聲、雨聲、海浪聲,草香、花香、泥土香,點滴沁人心田,讓詩人喜悅無限。
其實,華茲華斯生活的那個年代,是英國第一次工業革命崛起的年代;是經濟大幅起飛的年代;是蒸氣機替代人力與畜力的年代;是傳統產業逐漸式微的年代;是藍領階級與白領階級出現壁壘分明的年代;是人類對大自然的態度悄悄轉變的年代;也是人與人之間和諧關係,江河日下的年代。
老天是公平的,大地是講理的,朗朗乾坤,有得必有失。工業革命助長了物質生活,卻漠視了人文涵養;豐富了外境的美化,卻形成了心靈的匱乏;忙碌工作賺取了財富,卻失去生活的閒雅;欲望不斷擴大,卻失去人情的融洽,人與人之間的距離,從咫尺漸成天涯。
華茲華斯以詩人的浪漫與敏銳,一方面感受天地豐厚的賜予,一方面又反感於人際的冷漠、無禮、粗魯與對立。物質日豐,人情日薄;富者愈富,窮者愈窮;舊的階級尚未褪去,新階級又悄悄來襲,這都讓詩人憂心不已,一嘆三問:「人怎樣對待著人?」
詩人的驚天一問,我心戚戚,喚醒六、七十年前童年的回憶。雖然白雲蒼狗,時過境遷,心中仍有千千結,但答案爽朗在心,知道這個年頭,人是怎樣對待著人。
兒時年少,生活單純,在那普遍貧窮的年代,無需比較與計較,人與人相對平等。沒有高樓林立,土房竹籬,戶與戶間,或許隔著竹籬,但鷄犬相聞,人與人之間,相互聞問,人情甘醇。
那個年代,沒有豪華的百貨公司,沒有二十四小時營業的便利商店,但小雜貨店成了物流總匯,足夠滿足日常生活一切。
那時,沒有成群的摩托車,兩條腿就是最佳的交通工具,一部腳踏車就已讓人羨慕不已。
那時,也沒有呼之即來的小黃計程車,載客三輪車,車站市場列候,算是代步主流,區區幾元費用,也沒有多少人捨得乘坐。自用小轎車更是稀有,擁有的,不是殷商巨富,就是高官乘坐,官府所有。
沒有高速公路,沒有高速鐵路,鄉間土石夯成的道路,遇雨泥濘,日晒成土,強風刮起,車輛駛過,捲起飛揚塵土,行人迎來一團沙霧。
鄉鎮街道路燈稀有,日落送走最後斜陽,人們加緊摸黑趕路,幸好田埂小路,螢火蟲成群提燈照路,滿天星斗,皓月當空,草叢水邊,蟲聲蛙鳴,詩樣的微光微音,伴隨著行色匆匆的夜歸人。
那時,就業不易,少有稍具規模的大型工廠,遑論技術密集的科技園區,在民國四十、五十那個年代,台灣百廢待舉,農村鄉下,普通人家,農作之外,工作之餘,為增加收入,家庭主婦,男女老少,巧手細工,編織席帽,組裝飾品,響應「客廳即工廠」號召,發揮著民間巨大的生產力,有助外貿。
那個年代,電視開播沒多久,電視機算是稀有。報紙的銷售,因識字率偏低,知識分子是訂報的主力對象。收音機是當年傳媒的主流,家庭主婦一邊工作,一邊聽著廣播,歌仔戲,流行歌曲,有時唱個幾句,猶能琅琅上口。
沒有手機,當然難以想像現在的人手一機,家有電話,就已相當珍稀。大、中、小學沒有那麼多,能受教育就已算不錯。沒有太多的大小選舉,也沒有太多的口水對立,彼此溝通,南腔北調,各帶濃濃鄉音,比手畫腳,雖有些許語言的隔閡,但心存善意,倒也一團和氣。
沒有太多廚餘,大家都知道食物得之不易;沒有空氣汙染的問題,沒有生態環保的爭議,簡樸生活,處處可以呼吸到新鮮的空氣。
社會風氣純樸,鄉村小鎮,人人自謙是「草地人」,識字不多,見識不廣,見人總親切地說:「吃飽沒?來飲茶!」在那個年代,「食事為大」,能夠填飽肚子,討個茶水喝算是不容易,一句「吃飽沒?來飲茶!」是問候語,也是關心語,充滿樸質的人情味。
路邊的茶亭,大大的茶壺,寫著「奉茶」兩字,是善行,是心意,苦人所苦,關懷著從遠方一路走來的行人,哪怕和你素昧平生,路過就是有緣,口渴了,喝一杯,走累了,喘口氣,稍作休息,再頂著炙熱的豔陽趕路去。無名氏的善舉,把你當作尊貴的客人、遠方的親戚,用熱情默默地祝福你。那時候的人,雖然清貧,但人人都能將心比心,知道「人應該怎麼對待人。」
生命短暫,從呱呱哭啼、脫離母體而來,到告別人間、由親友哀戚扶柩而去。這期間,不論時間長短,不分世態炎涼,人生如戲,鑼聲響起,「你方唱罷我登場」。名聞利養,世事滄桑,成敗枯榮,驚濤駭浪,驚鴻一瞥,過眼雲煙,頓成泡影夢幻。
陳年往事,刻骨銘心的,不堪回首;瑣碎細節的,都已飄遠;平淡乏味的,逐漸淡忘。留下可以憶說的,僅是人生畫布上的彩筆一抹。
日落黃昏,夕陽的餘暉,似在回眸一整日的行程。日出的晨曦,正午的豔陽,日落的斜陽,都有它不可替代的風景。人到老年,營營一生,懷舊情結,油然而生,如同白髮宮女,愛說當年深宮的場景。
年輕人,對長輩的講古,也許已經可以如數家珍。老人家說到過去如何過日子,又是如何對待人,也許你也會不耐地說:「現在是什麼時代了,老是講過去!我都已經聽到耳朵長繭了!」雖百般不願,但還是請你傾聽,這是老人的婆心,應該得到善意的回應。
朋友說:「當你開始不停回憶過往的時候,你就開始老了。」
我說:「人老了,如果默然不語,那一定有病。」
回憶是每個人最珍貴的個資,是一生最後的資產。它將漫長的歲月,淬煉成簡短的箴言。
所以,當長輩在感嘆,在憶往,請讓他們暢所欲言,同理他們對人生來日無多的徬徨,對現實的諸多不滿。
更何況,今天你眼中的長輩,四、五十年後,就是白髮蒼蒼的自己,人人都有「塵滿面,鬢如霜」的一天。
大自然永遠良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在大化中,豈可抗天?人活在人世間,又豈可不情牽?
工業化、科技化、大數據、演算法,鋪天蓋地,帶來時代巨變。此時此刻,我們更應該時刻反省:人類應該怎樣對待大自然?人又應該怎樣對待著人?詩人的大哉問,我們必須積極作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