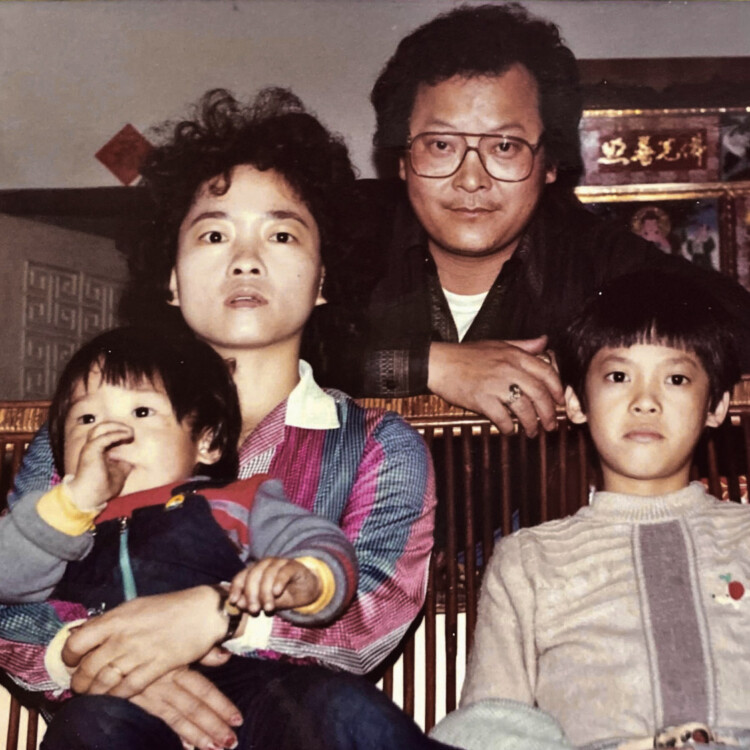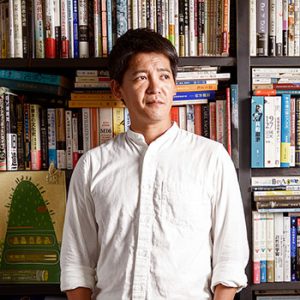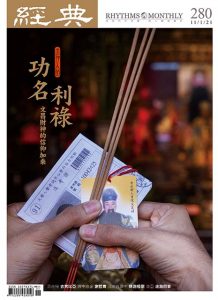故鄉,在現實與回憶中交錯,曾經以為澄澈清晰的,在追憶中化為粉塵,而那些自以為含糊未明的,卻以無比生動的方式,重現在我的眼前。
最近,我常常做夢,夢見南方的大海與天空,夢見港都的街道與巷弄,夢見許久不見,或今生無緣再見的人。
夢開始的地方,是港都靠海的那座山,在它南側的半山腰,有座讓許多人望而生畏的石階。
長長的石階盡頭,就是大大的平台,舊相片裡,殖民時代的鳥居不見了,改成了三座「一間二柱」的中式牌坊,回過身轉過頭來,就可以看見海了。溫煦敞亮的日子,可以遠眺港外的粼粼銀波在輕輕跳躍,夜幕低垂的時候,貨櫃碼頭的工作燈光,將大平台的石板映成沉銅昏黃。四五成群的少年囝仔,雙雙對對的親密愛侶,在各自的角落裡,喧嘩、呢喃。一百多年前,來自北方島國的統治者們,在以城市為名的山腰上,砌造了一座崇祖敬天的神社,又過了幾年,殖民政府將社殿遷至現在所在地,大半個世紀過去了,為南方子民奉公犧牲的勇者們,都被安置在石板參道盡頭的英靈殿。遊人們上到平台後,腳步大多在平台就擱淺了,對他們來說,眼前的光景才是永恆,瘖啞的過去,就讓它繼續沉默。
帶著牽掛的遊蕩
這裡,是高雄忠烈祠。
很久以前,台階下還有一座「大東亞共榮圈」的紀念石柱,多少寒暑過去,石柱上的日文與太陽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青天白日的愛國徽章。昔日肅穆莊嚴的廣場,今天有個很粉紅,多看兩眼就令人膩得想喝水的名字:壽山情人觀景台。
年少時,我常騎著那輛煞車不甚牢靠的自行車,搖搖晃晃,停停走走,從市區奮力騎上來。無視山下車水馬龍的塵囂,在山林中盤桓的公路,是城市邊緣難得的幽靜,濃郁的綠意,將溽暑蔭成清秋,往平台途中必經的小公園,無人問津的鞦韆與蹺蹺板,寂寞得無法擺盪季節的更迭。在梢頂飄搖的青葱,風吹過後,一地都是來不及撿拾的時間。偶爾,我會數著山徑旁爬滿苔綠的石燈籠,以鄉村搖滾的節奏,和緩緩地向平台攀昇,無論路線為何,目的是同一片天空,那片延伸至海平面盡頭的天空。
我曾不只一次站在這裡,望著大海,想像著這片湛藍的彼岸,有另一個世界,等待旅人的到來。有時,我會在這裡感受太陽,感受毒辣的熾熱,如感受那份讓血液也為之沸騰的灼烈。但是,更令我是心醉的,是夏季南方如瀑布般的暴雨。大雨來的時候,站在平台向城市望去,會看見如毛玻璃般的雨幕,重重地,沉沉地將城市鎖在雨中,呼嘯的風,傾倒的雨,一波又一波地,像浮世繪《神奈川沖浪裏》的巨濤一樣,撲向都會,摔在屋脊,沖刷整座城市。無論是將近四百公尺高的85大樓,或是咫尺見方的小哨亭,頓時都化為在汪洋中的小船,在駭人的洶湧中等待重生。即使,是雨水較少的冬季,雨依舊有它迷人的所在,灰色的霧雨,總是耐心地,有毅力地,一點一滴地,沒完沒了地下,濡溼每個港都人的靈魂。
在感受傾盆大雨片刻後,我會走下平台,沿著千光路、轉進登山路,來到山坳前碼頭。排排坐的高級遊艇,波紋不興的悠然景致,讓無心的人們遺忘,忘記這裡在很久以前,也曾經是東亞最繁忙的港口。
繼續往前,過了哨船頭,路會突然向右大轉彎,不稍加注意,左側「雄鎮北門」的紅磚城門在不知不覺就忽略過去了,因為,眼前的開闊更加引人注目。「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妝濃抹總相宜。」在舊時代人們的眼中,水光瀲灩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的一彎斜灘,在柿紅的餘暉中,有幾分西湖的妖嬌嫵媚,西子灣的名字就此而來。對於在港都生活過的朋友來說,西子灣之於高雄,就像是聖馬可廣場之於威尼斯、太陽門之於馬德里、第五大道之於紐約,是城市打開雙臂擁抱世界的大廳。我總在一天最寂寞的時刻,回到城市的客廳,坐在消波塊後方的石欄上,信手翻閱隨身攜帶的夢:鄭愁予、聖修伯里、白萩,惹內、余光中、村上春樹、向陽、卡夫卡、楊牧、葉慈……波浪化成文字,緩緩敘述少年對遠方的盼望,文字也化成了波浪,輕輕搖晃少年不成熟的幻想。我的目光,總在波光與詩間徘徊,漫不經心的等待:等待日光從熾白褪成酒紅,等待一個需要點點漁火的向晚,等待,白堊高崖上燈塔第一道劃破黑暗的虹晝,等待,來自薄靄中有家歸不得的嗚咽。
為賦新詞的傷春悲秋,望眼欲穿的鬱鬱寡歡,無以名之的磨損與幻滅,是我無用的青春中所能經歷最奢侈的揮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