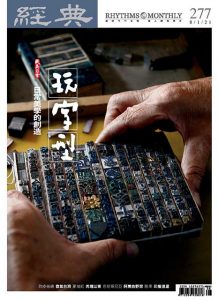首次拜訪他的家鄉台南中營那年,我二十歲。
烈日和大片嘉南平原一覽無餘的空間曝露感,以及他的大家族、眾鄉親那不分內外、無論早晚的人情黏稠度,都讓我莫名窘迫。
而後為人媳婦,我必須在年節及親戚婚喪喜慶時回去,勉強忍耐空氣中若隱若現的那股異味──混雜著泥土和魚塭的溼溽蒸熏,與豬雞鴨鵝養殖場散發的屎尿腥臊。萬一撞到農藥施打期,那陰森刺鼻的化學味更是逃躲無門。
總之,要認這小村作「家鄉」,並不容易。
不過,由於公婆相信「台北東西又少又貴」,而且「在地」又「著時」(當令)的最好,我們一年到頭依序收到滿箱滿簍的小村土產──春天黑豆醬油、蠶絲被,夏天芒果、龍眼、破布子醬,秋天柚子、酪梨,冬天菱角仁──因感謝公婆和這些四季恩物,小村多少漸漸親切起來。
後來他必須返鄉繼承家業,我也不得不把小村當第二個家,開始南來北往的日子。其中有四年因家事定居小村,回到都市竟一時不堪人潮車潮與噪音。
期間偶有朋友要來,一聽「中營」,大多啊一聲:「聽過新營、柳營、林鳳營,還有中營啊?」
我說「營」的典故是鄭成功駐軍屯田,再進一步說明屬於台南市「下營區」,但這只讓人更摸不著頭:「下營?還有下營!那有上營嗎?」
有,但那只是中營唯一一家7-Eleven的門市名稱。如此命名不知是否效法下營農會以台語諧音「A贏」(會贏)作號召,小七也要「尚贏」(最贏)一下?
外地人搞不清也難怪。台南縣市合併後,地址又改作「茅營里」,連貨運司機都被考倒,老繞圈找到昏頭。
從前有次搭計程車,我說了地址,司機說那在鄉下不管用,最好給個地標。就在東指西指終於到家時,司機好心交代:「以後別講中營,要講『茅港』啦!」
原來「中營」是統合四個小村的「官方說法」,當中包含在地人向來慣稱的中營、茅港,我們家所在地精確來說是茅港。目前這兩村被併為一里,故稱茅營里。
倒風內海與茅港
但明明是個農村,沒靠海也不臨河川,怎能叫「港」呢?
一追查方知此村不但曾經是個港口,還是被當時的人封為「小揚州」的大港口。荷蘭文獻、明鄭軍備圖和清代方志都有紀錄。
兩百多年前的台南海濱有多片沙洲與兩大內海,南為「台江內海」,北為「倒風內海」。台江內海是個潟湖,倒風內海則為狹長海灣。「倒風」應是台語諧音,指強勁季風把海水倒灌進內陸。在水路為王的年代,政經軍事據點多沿內海而建,當時倒風內海有四大港,「茅港尾港」(古時當地稱此海汊為「茅港尾溪」)是最大的一個,又位居台南府城到諸羅 (嘉義) 縣城南北官道中站,為四通輻輳之地,因而形成擁有五條主街的大都會,其中最繁華的「茅港尾街」還是人車分道的所謂「雙顯街」。
但好景不常,據我們家鄰居之先祖黃清淵先生所撰史略,一八六二年清同治年間某夜發生大地震,約兩百名居民喪生,街市一夕俱毀。村裡到現今還傳說是因為事發前日,街尾供奉的媽祖顯靈降乩預言劫難,結果居民以為將有盜匪來襲,皆嚴密釘鎖門窗,反造成逃生障礙與搜救困難,終致死傷慘重。
再加上後來急水溪、曾文溪改道淤積,失去交通優勢,茅港日漸沒落,到日治時代《台灣堡圖》上已無倒風內海,只是平原一片。光復後,新公路建設也另闢蹊徑,至此茅港已淪為邊陲偏鄉,甚至不再是中營社區中心了。
中營早年因乾旱多種番薯,受惠於烏山頭水庫和嘉南大圳後,才紛紛改種稻米,又因鄰近的六甲興起瓦窯業,四處挖購黏土材料,遺留的土坑便形成埤塘魚塭。直到現在,中營仍是典型台灣農村,居民多數務農,以種稻米、柚子,和養殖豬、雞、吳郭魚、泥鰍為大宗,也有些田地轉種菱角、蓮子,近年才見的作物則是酪梨、哈密瓜。聚落也維持傳統格式,以廟宇市場為中心,成集村住宅區,耕地果園養殖場都分散於外圍。時下流行切割部分田地蓋所謂「農舍」,此地倒不多見那款房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