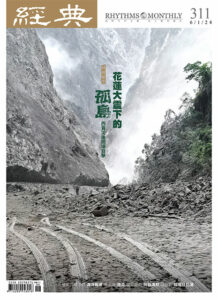有人問佛陀:「如何對待不喜歡的人?」
佛陀說:「報之以微笑,默默離開就好。」
又問:「如何對待喜歡的人?」
「真情流露,真誠相待就好。」佛答。
問:「如何對待別人的錯誤?」
答:「懂得寬恕,能夠原諒就好。」
問:「如何對待自己的錯誤?」
佛說:「勇於承認錯誤,敢於改正就好。」
問:「如何讓別人喜歡、怎樣被別人尊敬?」
答:「先喜歡別人,尊敬別人就好。」
事物相對,也彼此互補。
一位先知對他的信徒說:「我可以把對面的大山叫過來。」
信徒說:「真的嗎?我們拭目以待。」
於是,先知面向大山高聲呼叫:「大山過來!大山過來!大山給我過來。」
信徒滿懷期待,可是大山仍然如如不動,沒有過來。
正當大家心存疑惑之際,先知說:「大山不過來,我們就走過去。」於是他邁開大步向山走去。
「山不轉人轉」,不就是一個轉字。山不繞著我們轉,我們可以繞著山轉啊!叫大山過來目的不就是要彼此靠近嗎?誰過去,或誰過來,不都是一樣嗎?何必執著一定要大山靠過來。
這就是先知要告訴門徒「窮則變,變則通,通則達」的道理吧!
痛苦可以是一種折磨,也可以是一種昇華。
如果能全神貫注承受痛苦,就會發現原來痛苦並不可怕。如果能欣然接受痛苦,就會發現原來痛苦也是一種祝福的力量。
心念可以包容百種悲傷,產生萬種喜善,只要時時煥發清澄無染的正能量,凡事往好事想,痛苦是一種逆增上緣,恨也會向愛轉變。
奇蹟是一種神奇的力量,源於殊勝因緣,念頭一轉,世界變得不一樣,奇蹟就出現。
一念三千,三千一念,是苦是樂,都在一念間。慈悲是照亮黑暗的光,實踐能創造神奇的力量。踐行慈悲,就會顯得非凡。
有人問智者:「如何消除緊跟著自己的陰影?」
智者說:「只要你轉個方向,面對太陽就可以了。」
禍福自招,苦樂自找。事情,別人可以幫你做;吃飯睡覺,必須自己來。悲苦和喜樂,都是一種心態,看你是要背對太陽,或面向陽光。
宇宙浩瀚,不妨想像:你吸入的每一口氣,都是宇宙慈悲的供養,你吐出的每一分鼻息,都是能量的擴散。日沉月浮,地球也需要生息,節制欲望,才不會增加地球的負擔。
沉得住氣是一種了不起的才華,「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心若靜,處處都是美景,都是動人的畫面。
「遠看山有色,近聽水無聲;春去花猶在,人來鳥不驚。」是一首詩,也是一種意境;是唐朝詩人王維看畫的心得感言,讀其詩,猶如看一幅生動的山水畫。「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詩與畫相融了,人與詩兩忘,心中一片祥和平等乾淨。
一位聖哲對門徒說:「你了解事情無好無壞,也知道事情有好有壞。這是一件好事,也是一個轉捩點。從此以後,你開始學會內省了,也會開始向內心觀照。外界的一切事物,具有非凡的意義,也都毫無意義。一切都存在於你心中的選擇。」
這位聖哲一定是一個大澈大悟的人。他講的沒有錯,眾生平等,世間萬物,無好無壞。有好有壞是分別心。知道「真空妙有,妙有真空」,承認事物好壞的有無,不斷向內心探索,是件好事。
大千世界,朗朗乾坤,悲喜人間,喧囂社會,愛恨情仇,都是一部長篇巨著小說,一齣精采絕倫大戲。在小說裡、大戲中,每個人都是參與者,都是劇中人,沒有人是旁觀者。生旦淨末丑,都有人扮演,擔任哪一種角色,不是被指定,而是自己的選擇。演好自己慎選的角色,不要被負面激情所轉,而是主動轉動美善能量,人世間的結局就會不一樣。雖然個人的戲分總有落幕的一天,但人間大戲永遠會上演,莫說和自己無關,其實人人都是大梁。
善財童子要出門採藥,文殊菩薩對他說:「把不是藥的採回來。」善財童子領命出門。
過了不多時,善財童子空著竹籃回來,對文殊普薩說:「我看遍大地都是藥。」
文殊菩薩說:「那麼就把是藥的採回來。」善財童子又出門了。
不久後,他還是空著籃子回來,對文殊菩薩說:「遍大地都是藥,不知道要採哪一種。」
「只要是藥的,就採來。」於是善財童子就地隨手摘了一莖草,遞給文殊。
文殊菩薩拿起這莖草對大眾說:「這莖草能殺人,也能救活人。」
是的,大地的一切花草樹木,無不都是藥,也都不是藥。是藥,或不是藥,存乎一心的識用。
人世間無不是善,也無不是惡。是善是惡全憑一個正念。所謂「邪人說正法,正法亦為邪;正人說邪法,邪法亦為正。」心正了,念頭對了,是非善惡自然條條分明,待人態度和處事原則自然有分寸。
就像文殊菩舉起的那莖草一樣,能殺死人,也能救活人,就看拿在什麼人的手上、用在哪一個地方、而且知道怎麼用?所以能創造奇蹟的不是別人,而是自己,是自己心中的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