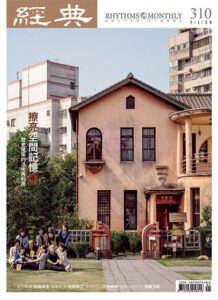清明時節風向轉變之際,北海岸仍籠罩在潮溼飄雨的天候。六十三歲的簡德源在三芝老家是第五代,守著一甲半的田地,水田耕作水稻與筊白筍,旱田則耕作少許蔬菜與果樹。磚厝牆上,「牧蜂休閒農場」的招牌同步揭示了這裡不僅是農莊,也有「蜂業」。在依三面山勢的農莊裡,簡德源擁四百五十箱蜜蜂,四月是中南部龍眼開花時分,簡家三個兒子已押蜜蜂大軍南下台中、台南採蜜,他獨守大後方,照顧少許留在家中的蜜蜂與種蜂──且慢!也許不是獨守。
「看到了嗎?」丹田有力的簡德源瞬間壓低聲量,悄聲說道:「『牠』站在那。」在蜂場沒間斷過的嗡嗡聲裡,一隻中型猛禽站在二十公尺外、約一層樓高的樹梢上,安靜睥睨,「牠在等我們離開。」他邁步走進蜂場,來不及眨眼前,猛禽俯低迅速掩入樹叢,剛才的現身彷彿一場人間幻覺。
蜂鷹──把蜂場當餐廳的猛禽
「我這邊出現這種『老鷹』大概二十多年。」簡德源說。簡家世代務農,簡德源在八○年代初退伍後,回家協助長輩耕作,深覺種田養家有限;家中本有養少許土蜂作家庭副業,他轉向大量飼養較溫和且生產力較高的西洋蜂,正巧搭上全台養蜂潮,也走入與「鷹」結緣的二十年。
養蜂在台約莫三百年歷史,早期多以竹、木為材料編織成箱,懸掛在住家簷下飼養,品種多為俗稱土蜂的野生蜜蜂,僅為家戶少量取食或貼補家用。日治時期,日人開始引入單位產量較高的西洋蜜蜂與飼養技術,希望替代部分砂糖的使用量;不過,戰後蜂業一度蕭條,直到國民政府有意識挹注資源,七○年代後養蜂產業才逐漸重新壯大。
農耕大環境的轉變,也助簡德源養蜂一臂之力。「那時稻米生產過剩,政府鼓勵休耕,農業轉工業也是風氣,許多鄰居到山下工廠,三芝農田荒廢下來;無農藥的環境,更利於蜜蜂採蜜與成長。」三芝本是看得到猛禽的好山水,農人生活中,抓蛇的(常是大冠鷲)、抓雞的(常是鳳頭蒼鷹)皆易目擊,無甚辨別,一律通稱老鷹,「不過會來蜂場的很少見、很奇怪。」他說起多年前的驚愕感。
猛禽來蜂場在看什麼、等什麼?
「看著食物、等人走。」長期在牧蜂農場觀測的台灣猛禽研究會理事張宏銘笑道,「蜂場是東方蜂鷹吃下午茶的地方。」揭露了廬山真面目。
全世界蜂鷹屬的鳥共四種:在歐、非大陸間遷徙的歐洲蜂鷹、只分布在菲律賓的菲律賓蜂鷹與只分布在印尼蘇拉威西的蘇拉威西蜂鷹,及廣布在亞洲東北部、日本、印度、東南亞的東方蜂鷹。
與大眾認知猛禽捕捉小型鳥類、鼠類、昆蟲為食不同,蜂鷹食性特殊,主食為蜂窩內柔軟的蜂蛹與幼蟲,也合乎牠們格外頭小、頸長、喙尖細的外型──利於啄食蜂室內的「好料」;雖然英文名為Honey-buzzard,但事實上,蜂蜜是不小心吃到而已,牠們也不吃蜜蜂。而為什麼張宏銘會戲稱東方蜂鷹來蜂場吃下午茶呢?原來,台灣養蜂人為收成時採蜜便利,會將蜜蜂築於蜂箱、巢片邊緣的蜂巢割除,蜂室內的幼蟲與蛹當然也不要了,有的養蜂人會將這些「贅巢」隨意棄置於地,無意間,竟發現開始有蜂鷹前來打牙祭。
台灣位於東亞澳遷徙線上的中繼站,二○○○年前,大部分賞鳥人總會在秋季的墾丁與春季的八卦山、北海岸觀測到「出海的」東方蜂鷹,認為牠們應是稀有過境鳥,雖墾丁的東方蜂鷹數量遠遜於數萬過境的灰面鵟鷹與赤腹鷹,但也有百隻上下。然而,這個眾人相信多年的認知,在二十一世紀初期逐漸被更多新的研究發現所挑戰。
「台灣猛禽研究會的研究員在十多年前有來過,問我們這邊有沒有蜂鷹。」簡德源的大兒子簡誌良回憶,因蜂場確有注意過來造訪的猛禽,樂於讓研究員進駐觀察,也進而揭開更多蜂鷹的身世之謎。
謎團一:蜂鷹哪裡來?
「雖然簡老闆跟我們說有,只可惜當時並沒有捉到牧蜂的蜂鷹做繫放追蹤。」猛禽會理事楊建鴻回憶。
楊建鴻二○○五年春天退伍,隨即加入中研院生物多樣性中心研究員劉小如團隊,執行與東方蜂鷹相關的研究計畫,「當時各地觀測紀錄不如現在流通,但有個重要的關鍵人物,生態紀錄片導演李偉傑。」楊建鴻提及,李偉傑是台中霧峰人,他回報研究團隊當地蜂場時常觀察到蜂鷹出沒,且不僅止於春、秋過境期,這個證言開啟研究人員的想像空間,進而疑惑長期以來對東方蜂鷹是過境鳥的設定,是否需要重新調整──李偉傑後也成為研究團隊夥伴。
其實,劉小如團隊並不是第一組疑心東方蜂鷹有台灣留鳥族群的研究人員。
一九九二年間,猛禽研究者林文宏便點名,魚鷹、遊隼、東方蜂鷹三種過境猛禽在台灣周圍國家都有留鳥,也許有機會在台發展留鳥族群;一九九四年間,鳥類生態研究者沈振中與黃光瀛相繼觀測到東方蜂鷹在北台灣有展示、護食與築巢等行為,但卻沒有繁殖成功證據。一九九九年,黃光瀛再次發現陽明山區的蜂鷹巢樹、幼鳥也成功孵出,這筆繁殖紀錄大大增加東方蜂鷹也許已有台灣留鳥族群的可能性,「因只有少數幾筆紀錄,當時尚無法肯定是否存在穩定留鳥族群。」楊建鴻說。
於是,二○○四年開啟的研究計畫,就以李偉傑的情報為前提,進入霧峰六十五個蜂場調查,「第一階段我們可確認的事實便是,當時十二隻繫上發報器追蹤的東方蜂鷹,竟一隻都沒有離開台灣。」楊建鴻指出,從二○○四年起,東方蜂鷹的研究工作持續十年,橫跨北中南蜂場,繫放超過百隻、追蹤也有五十多隻,一直試圖回答東方蜂鷹從何而來,要往何去的疑惑,卻事與願違。「每隻個體的回報紀錄都在台灣本島,有的會冬季在南方活動,繁殖飛到北方,有的終年都在中部活動、繁殖。」十年研究雖無法反推台灣沒有過境與候鳥族群的蜂鷹,卻確認了有穩定的留鳥族群。
而這段期間,東京大學鳥類學者樋口芳也追蹤繫放數十隻秋季離開日本往南方度冬的東方蜂鷹,發現南下軌跡基本上是沿中國沿海到東南亞諸國,台灣只是擦邊;再迂迴走中國內陸北返,根本不經過台灣。然而,這個發現也只能先破解日本飛出的東方蜂鷹,台灣不是主要中繼點。
在《111年度墾丁國家公園秋季過境猛禽族群調查計畫》報告中也揭露,「東方蜂鷹台灣族群遷徙屬性始終成謎……偶可觀察到過境群體中的部分個體於數十分鐘至數小時後折返往北,或有容易辨識的個體於一個月內重複出現的情形,但相同個體也經常在觀察數日之後未再見到……」更增神祕。
是否從某一年開始,原是稀有過境鳥的東方蜂鷹,突然決定留在台灣?也許正配合台灣蜂業大好的年代,也合乎養蜂人指認約二、三十年前開始看到猛禽造訪蜂場的說法?屏科大野保所教授翁國精以劉小如團隊當時採集到的初級飛羽做穩定同位素成分分析,初步確認台灣東方蜂鷹有兩個族群,一群為候鳥,一群為留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