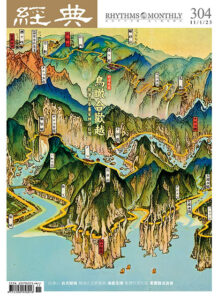辛亥路附近的台大學新館是棟新大樓,甫畢業的台師大生科所碩士林品萱站在館前,手持無線電發報器不時轉換方向測試,凝神傾聽傳來的「嗶嗶」訊號時強時弱。訊號聲最強的時候,她指著舟山路一側,放眼望去盡是系館、民宅與樹叢參差錯落的方向,「長頸鹿應該在那裡」。她邁步往前走,嗶嗶聲隨著她的步伐愈來愈強勁。
有「長頸鹿」正在人來人往的大學殿堂逛街?簡直要上新聞了!只是,這隻「長頸鹿」並非你心中浮現的那種長頸鹿,而是一隻二○二二年在台大校園誘捉,並追蹤快一年的成年母白鼻心。
「牠每次偷籠中的食物,脖子都伸特別長,前兩次都叼到食物就逃走,根本沒踩到踏板開關。」林品萱忍俊不住聊起誘捉這隻機靈貪吃鬼的過程。終於在第三次誘捉時,研究團隊把餌料綁死,貪吃的白鼻心必須認真踏入籠內才能吃到好吃的香蕉,這才順利捉到牠,繫上無線電項圈,追蹤牠在校園中的生活樣貌,並命名為長頸鹿。
山產或寵物──白鼻心獵捕史
正是大白天,傳回的訊號愈來愈強,巷弄間穿梭的林品萱停下腳步,在一棟老式透天民宅前肯定地說,長頸鹿在裡頭睡覺,這隻夜行性動物好夢正酣呢!民宅前芒果樹、蒲葵、蓮霧樹、正榕等老樹隨秋風搖曳,一位婦人推開家門,渾然不覺靜謐的老社區、空心連通的天花板、與源源不絕結果的樹種,吃好住好都讓牠極其舒適安心。這裡是北市大安區,台灣高度開發的首都城市,白鼻心入住的熱門選擇。
白鼻心是中型哺乳類動物,普遍分布在亞洲熱帶與副熱帶海拔二千公尺以下的林地,半樹棲型的牠腳爪與腳掌肉墊經過演化,特別擅於攀爬;體型修長似大一點的家貓,四肢雖然粗短,落地後仍可敏捷鑽跑,鼻心到頭頂貫穿一條白色縱紋是正字標記。
台灣白鼻心因第一上臼齒小於中國白鼻心,且毛色明顯差異,被學者分類為特有亞種。牠是食肉目靈貓科的雜食性動物,吃昆蟲、老鼠、鳥類等小型動物,也會爬樹掏鳥蛋,但更愛偏甜的漿果。食用方法是把果實含入口內擠壓果汁與果肉,再吐出果核與果皮。
台灣人所熟知的俗名果子貍、花面貍都依著白鼻心的習性與面部特徵而來,中文的「貍」指的常是野貓。白鼻心雖夜行害羞不親人,但也不特別畏人;在早期農業社會,白鼻心是果樹上偷食的常見鄰居,散見於許多散文作品中。國際自然保育聯盟(IUCN)列為無危物種。
睡在大安區民宅中的「長頸鹿」自在酣暢,但台灣史上的白鼻心前輩們,可沒有牠這樣的豪宅體驗──從一九八九年到二○一八年底,白鼻心都掛在保育類野生動物名單中,直到二○一九年移出名單。台灣人對白鼻心的認識與看見,也許是從「吃」與「玩」開始。
林品萱的論文是由台師大生科系教授林思民與台大昆蟲系副教授曾惠芸共同指導。林思民清晰記得一九七○年代,台北近郊的烏來山產店兜售的「肉貍」就是白鼻心;也曾在淡水、湖口等地看過有人用牽繩拉著或抱著白鼻心逛街。
「過去傳言,白鼻心有進補價值,當寵物養的人也所在多有,牠好顧好養、葷素不拘,所需空間不大,馴化後也可以帶出去逛,不太緊張。」林思民說。
從補身體到去汙名化
內服可以吃補,外帶足以炫耀,內外兼具的「功能」讓台灣曾有大量捉捕野生白鼻心的歷史,人工繁殖場也一度普及全台。
據已退休的台師大生科系教授王穎在一九八八年披露的山產店調查報告得知,當時訪查到的一百二十七個店家中,販賣白鼻心的達七十三家。貍血、貍鞭、貍肉、貍油都有人吃,肉用價格每斤六百元以上;貍毛可用以製作毛筆,也有人剝製標本。而活體販賣則視幼體或成體,當寵物、配種等用途不一,價格落在一千到一萬元之間,獲利空間實在不小。
「我還記得九○年代埔里的炊煙裊裊。」臺中市野生動物保育學會研究組組長林文隆說起往事歷歷在目。他清晰記得從高一起就每週日獨自坐著公車,搖搖晃晃地前進南投,替鳥會訪查山產店販賣的野生動物物種,籠內等待被宰殺的眼神、拉出籠外掙扎的哀叫,與煮水、烹飪的氣味交織,林文隆看著眼前景象,還未成年的高中生立志要走出野生動物保育之路。
同一時期,台灣也因野生動物獵捕、貿易、食用與藥用等議題惡名昭彰,頗受國際輿論壓力,催生《野生動物保育法》在一九八九年通過;白鼻心因獵捕壓力,第一時間就被列為珍貴稀有保育類野生動物,並列的還有穿山甲、石虎、山羌等物種。但除了一開始執法未見嚴謹,大眾觀望執法強度外,一九九四年《野保法》修法也為繁殖場與商家解套,白鼻心是政府公告可人工飼養、繁殖後且可販售的野生動物。
台大農經系名譽教授蕭清仁曾在一九九六年執行農委會(現農業部)委託計畫,調查台灣白鼻心的市場供需與經濟價值。他在結論指出,《野保法》發布後,合法登記繁殖的白鼻心仍在一萬餘隻之數,雖黑數難以追蹤,但隨著保育觀念逐步推廣到消費者族群,合法業者的買賣數量也在逐步降低,影響獲利收入,也讓飼養成本增加;另外,政府未鼓勵轉為經濟動物食用,也讓繁殖誘因減少,走向減量或停止飼養。
然後,當白鼻心再一次出現在重大新聞中,就是二○○二年了。
二○○二年底,從中國南方流行起來的SARS短時間突襲全球。第一時間的「禍首」據稱是查出染疫患者都在廣東野味餐廳食用過白鼻心,野生動物市場也驗出感染SARS病毒的白鼻心,中國因此大量撲殺。在緊迫與恐慌的情緒下,台灣出現棄養潮,養殖場一間間關閉。
這則流言在十年後才找到SARS真正的病毒帶原者是中華菊頭蝠,但揹了黑鍋的白鼻心也許是因禍得福,告別了人類的餐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