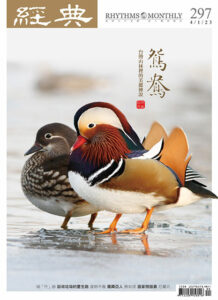冬日的汐止,總是陰雨。偶爾放晴,我的思緒彷彿穿過任意門,瞬間回到尼泊爾——我在三千六百公里外的家。
二十二年前的冬天,我初次踏上這片土地。還記得當時旅伴邀約,「春節假期一起出國玩玩吧!聽說冬天是適合去尼泊爾的季節。」當時的我其實不知道尼泊爾在哪裡、有什麼特色,只依稀記得「好像靠近西藏還是印度,感覺很古老、神祕,聽起來很酷」,我就答應了。我並不知道,生命會因為那趟旅行而徹底改變。
那個時候,還沒有什麼網路旅遊論壇、就連尼泊爾的旅遊書也少之又少,旅伴和我在行前幾乎沒做功課,只參考旅行社的出團行程,粗略地排了「尼泊爾旅遊金三角」——加德滿都(Kathmandu)、波卡拉(Pokhara)與奇旺(Chitwan),並在大致翻了《Lonely Planet》後加了兩天一夜的健行。排好行程之後,兩人就開始忙著年前的工作,直到因緣際會之下,朋友介紹了一位住在台灣多年的尼泊爾朋友,對方看了我們的行程,「排得很好,那你們住宿和交通都訂了吧?」這才驚覺,我們什麼都還沒做啊!於是那位尼泊爾朋友立刻打了國際電話給他在尼泊爾的「brother」,對方是旅行社老闆,就這樣搞定了我們的旅行。
住宿和交通安排都有了著落,旅伴和我於是好整以暇地等著出發日到來。也就因為毫無準備,我們在整趟旅程中幾乎都是狀況外。
我清楚記得深夜抵達加德滿都機場時,簡陋而昏暗的入境處,以及摸不著頭緒的簽證辦理流程與動線,讓我們茫然地呆站了好一會兒,好在旅行社老闆有門路,派了他在航空公司工作的「brother」進入管制區來帶我們;我也清楚記得每到一處,當我們開門下車,立刻被湧上的商販、司機與導遊包圍,著實讓我們緊張;就連在採買紀念品時,必須厚著臉皮、硬著態度跟商家們討價還價⋯⋯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從沒有過的經驗。
雖然狀況外,甚至在被人包圍時是有些害怕的,但絕大多數的時候,我面對一切的全新體驗都是舒服自在的。這可能要歸功於我的「老派」。明明是「六年級生」,卻對於父母甚至祖父母那輩的成長環境心生嚮往,當時在旅遊雜誌擔任編輯的我,「公器私用」地規畫了「小鎮之旅」單元,探訪了數個小鎮的發展故事,遙想它們曾有的繁華光景;也曾企畫專題報導,一口氣造訪數座糖廠,在老廠區散步,和老員工們話當年的過程中,拼湊出糖業曾有的繁盛面貌。於是,當我到了尼泊爾,那些看起來較台灣「落後」的市街地景與生活方式,深深地打動了我。
讓生命轉彎的奇旺
然而,真正讓我的生命道路就此轉彎的關鍵,應該是奇旺。
奇旺位於尼泊爾南部,在境內大多由高山、丘陵所盤據的尼泊爾,只有南部近印度處擁有敞闊的平原地形,而炎熱溼潤的氣候則孕育了茂密的熱帶闊葉林,許多動物在此繁衍生息。十九世紀,這片叢林成了尼泊爾的王公貴族的狩獵場,就連英國王室成員也曾來此打獵。隨著保育意識抬頭,一九七三年奇旺國家公園成立,在種種的禁獵與保育措施之下,一度瀕臨消失的獨角犀牛、孟加拉虎的數量迅速增加,此後更以生態觀察活動吸引遊人到訪。
當然,當時我也不知道這些,只是傻傻地跟著嚮導走,「我們即將進入叢林,這裡的一切都是天然的,我們不知道哪邊會有什麼動物,我會盡我的能力帶你們去找到動物、觀察動物。」嚮導接著說明遇到犀牛、老虎、懶熊等動物時的應變方式,「進到叢林,你們必須保持平靜。動物很敏感,如果緊張、害怕,動物是感覺得到的。」這一番話,讓我瞬間緊張認真了起來,小心翼翼地跟嚮導的步伐,在叢林裡鑽行著。嚮導則利用他敏銳的聽覺、視覺與嗅覺,尋找動物的蹤跡。行走的過程中,他也總要我們留意腳下,從腳印與糞便的大小和狀態,判斷是什麼動物在多久之前留下的。
對於在都市長大的我,這是全然陌生的體驗,我們不僅看到了犀牛、懶熊等動物,嚮導還帶我們爬樹看犀牛打架。因為實在太有趣、太特別,我們臨時更改行程,從奇旺到波卡拉健行之後又回到奇旺,也因嚮導一句「四月是最適合來奇旺看動物的季節」,腦波極弱的我們便瘋狂地在四月又去了一趟。
再次回到台灣後的我,時不時就想起奇旺、想起尼泊爾。我實在太想了解這個國家了,於是努力學習和尼泊爾相關的知識,只不過尼泊爾實在太冷門,搜尋到的資訊實在不多,我甚至還去學了以為很像但後來才知根本屬於不同語系的藏文。所幸,後來認識了在台灣讀研究所的尼泊爾人,每到週末,我們就在台大的學生餐廳裡進行尼泊爾文教學,在外人看來,這一桌的人念著陌生的語言、寫著陌生的文字,彷彿是什麼神祕組織。在反覆練習後,老師大力稱讚我的字就跟他寫的一樣,看不出來是外國人寫的。
我也總是逮著機會就飛去尼泊爾,並以「撰寫出版旅遊指南」合理化我的任性,並趁機練習尼泊爾文。因為閱讀了大量資料、認識了尼泊爾的發展歷程,這時的我格外著迷於加德滿都谷地各古城小鎮的悠遠文化,以及位於古貿易路線上的傳統市集的庶民況味。
沒想到,二○一二年我竟結婚並長住波卡拉,一個我在「金三角」三地中最無感的城市。
即便在婚前已往來尼泊爾逾十年,以為長住尼泊爾對我來說是小菜一碟,殊不知旅人和住民大不同,才新婚的我就猛然接受了震撼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