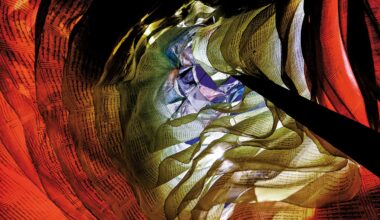我與長年在青藏高原合作的夥伴邱仁輝醫師及青海玉樹的東周視訊:主要討論因為當地的疫情封城,而我們這兩年固定的「馬背上的醫師」視訊培訓是否如期舉行等等。
很不習慣用視訊的方式與藏族朋友碰面,因為與藏族朋友碰面多是在四千公尺海拔的青藏高原,總是享受特有的清新空氣與藍天白雲的情境,也因常年高原紫外線曝晒,藏族朋友大都有著黝黑的膚色,同時帶著一股濃郁的酥油味,這些是視訊裡聞不出也看不清的。
在青海的「馬背上的醫師」培訓計畫,是從青藏高原東南部四川理塘縣的計畫轉移。原本始於一九九五年的醫療培訓,當時仍是貧窮與封閉的青藏高原東南部,我們努力與縣衛生單位合作,希望能解決多年來「缺醫少藥」的窘境,培養第一線的鄉村醫生是當時持續任務,直到二○○八年,竟也為約台灣四倍面積的甘孜州培訓出三百多位的鄉村醫生,我們稱他們為「馬背上的醫生」。
隨著四川經濟的發展,窮鄉也慢慢寬裕,原計畫每村都有醫生的目標也幾乎達成。於是我們轉到更偏遠的青藏高原可可西里,就是青海玉樹州的西北部,由原先培訓鄉村醫生,改為提升既有鄉村醫生的醫療專業為主。然而,因近年疫情持續,我們計畫一度被迫中止,但藉由全世界都興起線上授課模式,我們終勉讓計畫持續著。
當年從四川轉到青海是有些無奈也很難割捨,知曉爾後不會再專程前來,也不會再呼朋引伴特意將台灣的贊助計畫者帶來此地。方案的結束,就代表生命中的一段歷程的終點,終於安排了一場巡禮來斷捨離,也對這片一九九○年起陸續造訪數十趟的土地投以最終的致意。
我刻意花了較長的時間到縣城上方的寺廟裡轉轉,長青春科爾寺於一五八○年由第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創建。長青春科爾為藏語譯音,「長青」意為彌勒佛(即未來佛),「春科爾」意為法輪。九○年來時即認識了香根活佛一家,也熟悉了寺廟永遠瀰漫著的酥油燈味。僅要時間許可,我都會來頂禮寺裡三層樓高的彌勒佛像。
八○年代中期開始,隨著某種程度容許的宗教自由,我見證了藏區的寺廟不停地大興土木,當然也更加金碧輝煌,長青春科爾寺當然也在這波潮流。我進入整建中的大殿,殿裡座座嶄新的鎏金佛像並沒喚起我的興趣,反是秩序井然的民工背著一簍簍的水泥漿正魚貫地進來,引起了我的好奇,一問之下才知他們全是志工。這些藏民布施著他們的時間與勞力,對他們心愛寺廟能擴大規模無不法喜滿滿。我踏出寺廟,外圍是一波波順時鐘繞著瑪尼石堆的信徒們,他們口中誦著經文,手中轉著瑪尼經輪,我拍了些照,也學著走累的老人家坐在一旁休息。是為今世懺悔?或為來世植福?我一直被這種浮囂人間的某種單純的氛圍吸引,僅要虔誠,這裡就是通向美好未來之途徑。
我跟邱醫師驅車到縣城以西的毛埡壩,剛好是長青春科爾寺的僧侶在此為鄉民念經祈福,舉辦了場為期三天的法會。草原邊上搭了一頂百來坪大的白色帳篷寺廟,後方則排列著十餘座供住宿的白色帳篷,而帳篷寺廟旁還特別搭了一個三十坪大的犛牛毛帳篷廚房,裡面放著五張大小不一的大圓鍋,料理參與法會的上百僧侶的三餐飲食。毛埡壩因著這場法會,原先游牧的藏民紛紛將各自的帳篷聚攏,一時間,雜沓著牲群與人煙熱鬧了原本寧靜的草原。
這片草原累積了我十幾年的回憶,走踏其中回憶湧現。從一九九四年在甘孜州遊走尋找計畫的實施地點,來此時一路被後頭的風雪追襲,回頭所見白塔上的彩虹(見《經典》雜誌第二八○期),也因此理塘成了計畫的實施點。此時溫暖的陽光同樣灑曳在白塔上,我想旁邊的邱醫師一定相信這場告別是被祝福的。
格聶神山海拔六二○四公尺,是沙魯里山脈的最高峯。它的藏語名為呷瑪日巴,藏傳佛教二十四座神山之一,也是勝樂金剛的八大金剛妙語聖地之一。格聶神山和旁邊的肖扎神山之間的谷裡,是有名的冷谷寺。多年前曾領著台灣夥伴們騎馬露營拜訪過。當時即盤算將再回,我也事前囑託理塘的伙伴鄧珠,找好嚮導與馬匹,我們取道新路線肖扎神山的右側兔子溝谷地探訪。
將帳篷睡袋與食物打包在馬匹上,我可比不上鄧珠的熟練。騎馬在人煙罕至區的探索,彷彿很是浪漫,然而剛跨上馬背上的興奮,幾小時後就會因酸痛的臀部不堪折磨,而期盼著下馬休息;但四千多公尺海拔的高原本來行動就會受限,更何況上坡更不容易,於是上下馬之間總有一番掙扎。兔子溝谷地兩側的山丘有些天然山洞,稍加整修,再圍些簡單的圍籬,嚮導阿克尼瑪說是喇嘛修行閉關之地。溪谷地邊有溫泉,策馬入森林又是另一番挑戰,果不其然,冷不防就被小徑的松木橫枝給掀下馬。我聽到懸崖上一陣窸窣聲,抬頭一看,為數約四十頭崖羊在峭壁的灌木間覓食,嘗試取出相機,但牠們整群迅速消失不見。我們紮營於溝邊,滿空星子,一彎弦月,伴著溝火,原本有些傷感之旅,當下卻是滿足無比。
「沒有任何詞語可以形容這座高大的山峰,在這裡任何旅行者都可以體會到藏人的心情,不由自主地稱之為聖山……」一八七七年英國探險家威廉吉爾(William Gill)來到格聶,在他的《金沙河》一書裡留下這樣的讚嘆。拜時代的進步,我不用像吉爾領著六十人的苦力,探險隊伍才能從康定出發經此二十四天後抵達雲南的大理。回憶著九○年代初期,單從成都出發,即使沒遇到泥石流等天災,也要四天的吉普車顛簸才能到此,而如今隨著公路的改善可節省一半時間。但摒開公路的改善,無公路的鄉間進步幅度仍是緩慢,電力仍未扺達,手機仍是無訊號,這些地區也正是過往所陪訓的馬背上醫生的重點工作區域。
翌日我們騎馬翻越山稜上攀到五千公尺海拔的肖扎山麓,山稜上可見牧民所搭的風馬旗,也有幾頭家犛牛來此覓食。天空上盤旋著禿鷲與老鷹,百靈鳥則在四周輕盈穿梭。格聶山群峰格聶山居於左,中為肖扎神山,右邊克麥隆神山。我們橫切山區,一行上上下下,時而體會稜線上的十級冷冽陣風,一會兒又進入林區聞著清新的芬多精。
我曾在《在龍背上》一書中寫著:在青藏高原的旅行一直沒有終點。在醫療計畫執行時,資金的籌措、人員的行政後勤、與對岸政府的對應,總是堆滿許多挫折。但說也奇怪,這些煩惱僅要上到高原,就成了過往雲煙。長青春科爾寺的好友活佛羅卻佩曾說,我在做一件一輩子想起都會笑的事。也許是對的,在應付大都會的日常瑣碎中,我仍慶幸仍有一片空間去遨遊。一趟趟高原之旅,彷彿有著小叮噹的任意門,自在地在二十一世紀與十九世紀間穿梭。
於是在理塘的終點,在可可西里就是另一個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