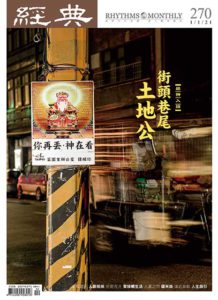每一種建築樣式,都是一種對幸福的理解;建築為我們遮風擋雨,也讓我們看到,屬於自己的理想人生。
——艾倫.狄波頓(Alain de Botton)
「這房子剛買的時候,一共隔了五間房,不管怎麼轉身,總覺得看到的都是牆壁。」今年五十六歲的Carroll,前半生分別在美國、日本與新加坡度過。住慣了寬敞環境的她,在孩子長大後,決定落腳台灣;搬進新屋後,她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敲掉既有的格局,改成自己喜愛的樣子。
相對於Carroll,四十四歲的OL孟晚周,住所的室內只有十五坪,但小小的空間,已足夠她在無數的清晨與黃昏,感受到盈滿的小確幸。
「除了看到窗台上的盆栽開花,會感動莫名外,社區外的步道可以散步,社區內的游泳池、健身房,可以省下可觀的運動花費;有圖書管理員的圖書館,把書借回家不算什麼,酷的是住戶還可以表達選書的意見。」對孟晚周來說,量身打造般的公設,大大地彌補了空間的不足。
再把鏡頭轉向同一棟集合住宅裡,另一戶透著微光的溫馨小屋,五口之家的林仁德對於幸福的定義,首重安全。和太太育有三個孩子的他說,「因為住在高樓層,避震是一定要的;其次消防灑水系統的裝置、停車場的動線,管理費的運用方式等,也都在考量之列。」
所以可以這麼說,儘管每個人的背景、需求不同,但對於幸福建築的想像,無非是建立在環境上的安全、設計上的美感、功能上的完善,以及生活上的便利等。
就這點而言,近二十年來的台灣,除了住宅形式更多元:有近兩成的公寓(指全台,雙北則各約五成),近三成的集合式住宅,近五成的透天厝(多在中南部),以及少數形式不一、自地自建的農舍外,在品質與安全上,歷經九二一大地震的震撼教育,新建物在新法規的要求下,從避震、消防到汙水處理等,都較以往有長足的進步。
所以,暫且把仍然有待解決的問題放在稍後討論,如果我們知道眼前的一切都不是理所當然,而是歷經曲折才走到這一步時,珍惜之餘,或許我們也才對未來敢於想像,並有勇氣往更圓滿的幸福邁進。
公共與住宅的建築地景
居住是人類的基本需求,建造合宜的住宅,是建築的核心,然而,這個簡單的道理,卻不是所有人一開始就懂的。
「早年國民政府剛來台時,沒想過要落地生根,因此對於建築,基本上是沒有太多規畫的。」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吳光庭表示,「所以當年本來為數就不多的建築師,手上的業務,幾乎都以商業為主。」
但商業的本質在於降低成本、追求利潤,也就是將建築的坪效極大化。在業主的要求下,建築師往往躲在幕後,淪為畫圖和結構計算的工具,只有極少數頂尖的建築師,才能在公共建築裡找到發揮的舞台。
大約在一九五○到六○年代間,由當時號稱台灣三大建築師:盧毓駿、黃寶瑜與修澤蘭等分別設計的國立台灣科學館(今國立台灣科學教育館)、中山博物院(今故宮博物院),以及陽明山中山樓等,即是此一時代背景下的產物。
只是包括國父紀念館與中正紀念堂在內,這些公共建築所服務的對象,都是政治上的權威,而非一般大眾。元智大學建築系教授阮慶表示,「此外政府工程的起造流程、品質控管、款項申請等,往往都冗長而繁複,這對於有滿腹理想的建築師來說,還是常會有綁手綁腳,施展不開來的感覺。」
商業大樓與公共工程如此,與民眾最相關的住宅,則緊扣著台灣人口的成長與經濟的發展。
因應一九四九年的政治移民與戰後嬰兒潮,政府先是利用日治時留下的宿舍或另行興建眷村,安頓數百萬軍民;接著,在一九五七年頒訂《興建國民住宅貸款條例》,提供長期低利貸款興建國民住宅後,直到一九七九年左右,台灣的國宅計有一萬兩千多戶,但總人口數卻逾一千八百萬。
人口的暴增(在少子化的今天,大家可能很難想像),導致兩種結果,一是擠不進去的人只能自力救濟,違章建築,成了城市獨特的景觀;二是隨著經濟起飛,股市上萬點,台灣的房市也迎來第一波的榮景。
但一如這陣子台灣營造業的狀況,台商的大量回流,造成廠房的急遽短缺,一時間,閒置多時的土地,紛紛大興土木,建築工人與原料,成了最搶手的資源……只是當年在建案暴增,缺工、缺料情況嚴重下,不良建商回應的方式卻是偷工減料,甚至以會造成鋼筋腐蝕變形的海砂當建材,在原本就是地震島的台灣,埋下了悲劇的未爆彈。
站在完工於一九八四年,卻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二十一日的凌晨,在大地劇烈搖晃下,一夕間應聲而倒的東星大樓原址前,一如其他同時受損的建築,它也早已完成重建,一樓的百貨商家人來人往,但曾有的傷害,卻在當年的居民內心留下陰影,並成為全台灣人難以抹滅的記憶傷痕。
所幸,台灣社會一直不乏反省的能力,正因為九二一帶來的傷害是空前的,台灣的建築史,也才有機會翻向全新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