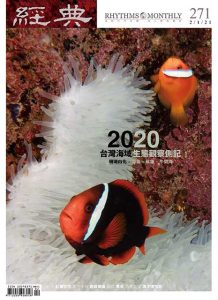走出台北市圓山捷運站,步行幾分鐘即可到明倫社會住宅,建築物以粉色調的藍、黃、紅三色組成,明亮溫暖。寬廣的中庭旁有即將招生的幼兒園、社福空間,拾階而上,二樓廊道鋪上紅色跑道。
明倫社宅不僅公共空間充足,各個房型也都明亮通風。然而三房型三萬六千元到四萬零五百元的租金引起熱議,輿論認為租金過高,不符照顧國民居住需求的初衷。然而抽籤截止後,申請者仍是遠超過提供的戶數,反映社會住宅供不應求。
其一源自目前的社宅量遠遠不足,二則反映台灣民間購屋及租屋的大不易。
望房市而興嘆,促成社宅興起
一九八九年的無殼蝸牛運動要求政府打房,然而三十年過去,房價所得比卻從當年抗議的八.五八倍,到二○一九年的近十四倍,形同要「十四年不吃不喝才能在台北買房。」合理居住愈來愈難實現。
六十餘歲的徐金濱、陳麗珠夫婦見證了這一段。白手起家的他們利用住在出租國宅的十餘年,存下了購屋頭期款,買了台北松山區國宅。十年前,好不容易繳完二十年的國宅貸款,想接續幫成家的兩個兒子各買一間房時,然而房價飆漲,有限能力只能再買一間,「而且是我們父子三人一起揹房貸,才買得起。」徐金濱補充。該是頤養天年的年紀,卻仍在繳房貸。
根據去年第三季最新資料,六都的房價負擔率都超過收入三成的合理負擔,台北更是高達六成。台灣都市房價高不可攀,然而許多人仍前仆後繼地投入購屋市場,台灣的房屋持有率這十年都在八成四到八成五間。
除了有土斯有財的觀念根深蒂固,政策一方面希望住者有其屋、鼓勵國民買房,一方面卻又持市場萬能論,而非加以管控,都讓房價高速飆漲。
台灣持有房屋的地價稅、房屋稅都低(台灣地價稅僅是美國的十分之一),讓房子成為極佳的投資標的,因此儘管有許多人買不了房,但也有人名下卻有好幾棟房子。據財政部資料,全國約六百八十一萬個家庭持有房子,約38%家庭持有兩房以上,7%家庭則有四房以上,十戶以上的則有千分之四.四。同時也約有八、九十萬間空屋。
「高房價是各國都碰到的問題。但跟國外房子需求大於供給不同的是,台灣因為持有成本低,有很多房子空著,不賣也不出租,儘管供給大於需求,卻仍是高房價。」OURs都市改革組織祕書長彭揚凱說。
此外,租屋市場不透明也不健康,成為一大推力,許多人都經歷被無故漲房租、房東不願修繕等租賃糾紛,因此儘管面對咋舌房價,仍期望有生之年有自己的房,「且房租繳給房東,不如拿來繳房貸。」
「國外,租屋也可以是種居住選擇,不一定要買房。但台灣的租屋黑市,逼得所有人要去買房子,也更加拉高房價。」「若房客被房東趕過三次後,大概就立志要買房子了。」彭揚凱說明。
過度市場導向的房地產、不健康的民間租屋市場,都解釋了為何每當社宅開放申請時,都成為搶手的居住選擇。
僧多粥少的社宅
但社宅量遠遠不足需求量,仍是重要關鍵。
據社會住宅推動聯盟去年十月統計資料,全台社會住宅存量近一萬七千戶(未加入包租代管),是全台灣近九百萬戶住宅總量的0.189%,不到千分之二。
如果蔡英文總統在任期屆滿前,蓋完十二萬戶社宅,仍只達到1.3%,加入包租代管的八萬戶,也僅是2.2%,不僅無法與香港、荷蘭的30%相比擬,連與日韓的5、6%都有一大段差距。
存量遠遠不足,來自台灣遲至二○一○年才開始推動,日本推動了半世紀以上,連晚發展的韓國都比台灣早了二十多年,「我們像十歲的小學生,歐陸社會卻已經是一百多歲的人瑞了。」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形容。
「台灣錯過了經濟好的一九九○年代。」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黃麗玲分析。同時高度都市化也讓找地日益困難。
近年各地社會住宅陸續興建完工,新穎的建築設計,低樓層更結合托老托幼、居民活動等多功能空間,造福社區,翻轉過往擔心社宅可能是「鄰避設施」的印象,吸引搶租。除了硬體,租金普遍比相似房源便宜,房東、房客的權利義務規範清楚等,都構成「一房難求」的要素。
只是在僧多粥少下,社宅照顧了最需要的人嗎?
「我們社宅量是世界上數一數二少的,入住資格卻是世界之寬。」彭揚凱說明。相較各國推動社會住宅初期,都是以照顧弱勢者為主,隨著社宅量增加,才放寬入住資格,台灣卻是在開始即將收入條件訂定在50%以下,從無收入到年收一百四、五十萬元都可申請。「這就像只有一、兩桌菜,卻邀請數百、數千人來吃飯。」呂秉怡比喻。
資源如此有限卻大方地發送,源自台灣現今面臨的居住問題更加嚴峻,「現在社會窮的不只弱勢者,也包含年輕人,高齡化同時更加嚴重。要照顧的群體更多,國家資源卻比以前更少。」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副教授黃麗玲分析。
除了入住資格寬鬆,弱勢比例也有所限制。《住宅法》規定弱勢戶至少需占三成以上,然而最低標三成卻成了各縣市訂定的天花板。政府希望用三比七的弱勢戶與一般戶混居方式,讓社宅不被當成貧民區抗議,得以順利興建。然而當社宅未來達到二十萬戶,也只能照顧六萬多戶的弱勢者,遠遠不足全台灣三十幾萬戶的弱勢家戶。
其實也仍有隱藏的選舉顧慮,「二十到四十歲的年輕人屬中間選民,最易受公共政策影響投票意向。」呂秉怡說。「最開始只有10%弱勢戶,那根本是玩假的。」黃麗玲說。
「美國是housing first,先把人安置好、身心安頓,再談社會救助。社宅應該是種社會救助網。」黃麗玲強調,居住安穩對弱勢者格外重要,「現在應該不太有社宅汙名化問題,且弱勢者定義很廣,多子女家庭也算。要開始適時提高弱勢者比例。」推動社宅誕生的倡議團體提醒,花費最多資金興建的社宅,應逐步釋出更多比例給最需要照顧的群體。至於年輕人或非真正弱勢者的居住問題,應以其他政策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