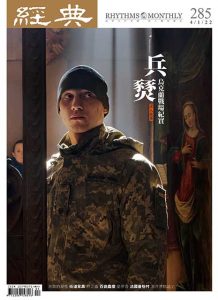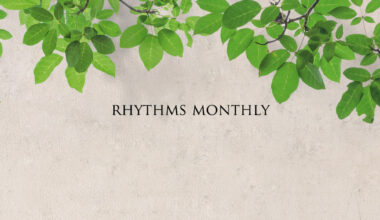最近在《醫病平台》發表了一篇文章,談及自己初到美國時,深深感受到語言溝通的困難,嚴重影響到醫病關係。想不到一位過去教過的學生,來信說他看到這篇文章十分感動,「我想起以前教授在課堂上說過Charley horse的故事,很有啟發性 」,使我忍不住寫出這篇文章。
這位學生提及的「故事」發生於我剛到美國沒多久,我為一位病人做腰椎穿刺(lumbar puncture)時,在局部麻醉下將腰椎穿刺的長針插入病人背部時,他突然迸出一句「Oh, Charley horse」。
由於做這種手術時,病人是側躺在床上背對著醫師,所以彼此看不到臉部表情,而偏偏在這關頭,醫病雙方發生語言溝通的困難。我一時愣在那裡,想不通他講這句話的意思。我知道horse是「馬」,但我停下來左顧右盼,怎樣也無法理解在醫院這環境怎麼會冒出與「馬」有關的話。再三思量還是不解,只好繼續穿刺的手術,看得出病人非常不滿。
我在做完穿刺後,囑咐他需要絕對臥床六小時以免腦脊髓液滲出而引起「脊椎穿刺後頭痛」。他一直餘恨未消地喃喃自語:「你怎麼可以在我告訴你我有Charley horse時,還繼續做穿刺!」
我回到醫護站將抽出的腦脊髓液分別裝入不同試管,貼上送往感染科、生化科、細胞檢查的標示以後,我禁不住問一位護理師,Charley horse是什麼意思? 她好奇地問我,為什麼突然問這美國人慣用的俚語。我告訴她整個情形,她驚訝地說這句俚語意思是「抽筋」,而我在這種情形下,還繼續做穿刺的手術,難怪病人會生氣。我聽了之後非常不安,忍不住問她,「你們美國人怎麼會把這叫做Charley horse?」她靦腆地回應,「我也實在不能怪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