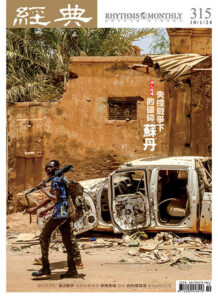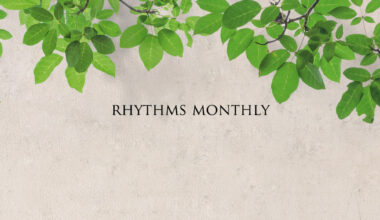我一生堪稱樣樣如意,但是我在一九七五年初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醫院所經歷的最初兩年住院醫師訓練,卻是我有生以來最失意的低潮。
我在大學畢業之後,因為想做精神科醫師,進入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做完四年的住院醫師,想不到經過種種機緣,發現我對神經科比精神科更有興趣;本來想做神經科而進入同一科的慢我兩屆的學妹,後來也發現她對兒童精神科更有興趣,婚後我們就改變了生涯規畫,在台大醫院神經科洪祖培教授的安排下,我有機會到明尼蘇達大學的神經科主任貝克教授(Dr. A. B. Baker)的住院醫師訓練計畫受教兩年,而內人也申請到同一醫院的兒童精神科研究員,而展開了我們的美國之旅。
然而我們到美國的最初幾年,卻嘗盡了人地生疏之苦。回想起來,也深悔當時到美國之前並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尤其是在語言、生活方面都沒有好好下功夫,更是一大錯誤。譬如說開車這件事,我是在出國前幾星期才學會開車,拿到台灣的駕照;換了國際駕照就「勇敢地」在美國開始開車上班。當時台灣還沒有高速公路,可想而知地,上班開車到了醫院已是冷汗浹背、精疲力盡。本以為自己的英文在說、寫、聽應沒有問題,想不到第一天上班就發覺,我不知道講了、聽了幾次「beg your pardon」(「對不起,能否麻煩你再說一次」)。
病人的照護更使我不安。本以為自己在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已經做完四年住院醫師、一年主治醫師,照顧病人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但是第一天與病人及護理人員接觸時,就因為無法完全了解別人的話,或讓對方瞭解自己說的話,尤其是美國人的俚語(slang)使我產生許多誤會,這才知道醫病之間的語言暢通,遠比醫學知識更重要。唯一值得欣慰的是,我習慣掛在臉上的笑容,倒是幫了我不少忙。
同時,病人出院時的病歷摘要是以「聽打」的方式,用英文對著錄音機整理出病人住院期間的病歷,再由負責聽打的祕書打出來。我一看她打出的文字裡有一大堆的空白,而且她非常耐心地問我好幾個字的拼音時,我的心情低落到極點,面對這位小心不願傷害我的自尊心的祕書,更使我慚愧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