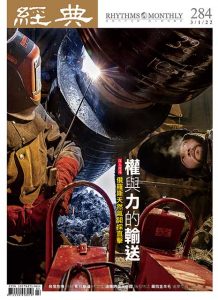「陽台是室內、室外的邊界,一如海洋和陸地之間有潮間帶,兩個不同空間重疊的地方,生產力總是格外地旺盛。」
陰雨連綿的春天,來到樸門永續生活工作者林雅容的家時,偌大的陽台,印證了她的這番說法。遠處的群山蓊鬱蒼翠,眼前的絲瓜、火龍果、迷迭香等生機盎然;如果把後陽台所養的一窩鵪鶉也算進去,她的陽台生產力,果真不是蓋的。
但林雅容所謂的「生產力」,遠不只是花果家禽。自從搬來這處有著十坪大陽台的新店新居後,在屋裡待倦了,到陽台喝杯茶、看本書,一下子疲憊全消;十歲的兒子阿豆想看只在夜裡綻放的火龍果開花時,一家三口把晚餐端到陽台,邊吃邊慢慢等待,其樂樂無窮。
事實上,陽台作為建築物的元素之一,最早是西方的統治階級為了凸顯尊貴的地位,被設計來居高臨下,俯瞰芸芸眾生之用。類似的功能延續到君主制度瓦解或轉型,一般的民眾也能擁有屬於自己的陽台,除了具有通風、日照,洗衣、晾衣的功能外,電影裡常看到的畫面:站在陽台上和隔壁鄰居聊天,對著鵝卵石街道上匆匆走過的少女吹口哨,這一切都讓義大利的漫畫家馬可仕(Marco Dambrosio)戲稱,陽台是最早的社群媒體。
回到台灣,早年除了部分原住民族有著可以遠眺的高腳屋外,以閩南風格為主的漢人建築,並沒近似的建築單元。日治時期,除了少數的富商,如大稻埕的陳天來與李春生他們的「豪宅」,建有寬敞的西式陽台外,自清代就有的街屋,多了引自西方裝飾風格的精緻繡面與花台,有那麼一點陽台的味道,卻又還不足以稱為陽台。
國民政府來台後,為了安置暴增的人口,國民住宅興建委員會利用美援,在六○年代初蓋起了立體分戶式的「公寓」,這種全新款式的住宅最大的特色,是配合「兩個孩子恰恰好」的生育政策,規畫有三房兩廳之外,也誕生了與當代風格最接近的陽台。
根據一九六一年由台灣省公共工程局所出版的《台北市示範住宅》一書所寫到,當時的陽台就已被區別有景觀休閒與晾衣之分,是所謂的前後陽台;而隨著科技的演進,有的設備出現後又消失於後陽台,如瓦斯爐(改為天然氣);有的則成為「標配」,如洗衣機、冷氣主機(窗型改成分離式);直到七○、八○年代起,為了將使用坪數極大化,許多住宅外推的不只是後陽台,也包括前陽台,在換得額外的一間臥室、餐廳或廚浴的同時,卻也有人把它拿來堆放雜物,使得原本應該明亮、通風、行走順暢的陽台,淪為室內最凌亂的倉儲一角。
半戶外、半開放的獨特空間
「實在很可惜,因為在當代都會生活中,如果連陽台都消失了,那就等於我們在家裡唯一能接觸到大自然的窗口,也被關上了。」室內設計師黃世光,作品向來重視打造健康的環境,他以為,好的住宅必須兼具採光、通風、溼度與溫度的調節,「而這些功能都可以藉陽台而達成。」他說。
所幸,近年來他觀察到,一來是社會高齡化下,不少長者待在家裡的時間愈來愈長,陽台成為他們蒔花養草、打發時間,接觸外界等一個不可或缺的平台。二來,對年輕世代而言,陽台除了實用性不變外,重視在工作與生活間取得平衡的他們,更喜歡把它打造成兼具美感,並且能與三五好友談心聚會的社交空間。
坐在一張舊沙發上啜飲著咖啡,自由接稿的美編李佳雯,把陽台打造得就像一座迷你咖啡館。在她旁邊,好友兔子踩著運動器材,兩人偶爾會聊上幾句。在這以高密度人口著稱的新北市板橋區,一處距離傳統市場幾步之遙的老公寓裡,沒有後陽台僅有前陽台的她們,卻因為收納得宜,在安裝了洗衣機、冷氣主機、電動晒衣架與電表之後,竟然還有餘裕,能再擺上一張雙人沙發,一只矮几,一架洛克馬攀爬機以及三十多盆的盆栽。
至於五十五歲的黃玉蓁,找了兩年多的房子,最後選擇新北市紅樹林一棟屋齡十二年的大樓九樓,作為今後的養老之所。沉浸於綠拇指之樂、重視生活美感的她,每天都要花上幾十分鐘甚至幾小時,悉心照料一坪半大的前陽台上,超過六十盆的琴葉榕、變葉木、多肉、九重葛等植物,最愛陽台內凹設計的她說,「它能承接光照,又不致於讓高樓特有的高壓風直接狂吹。」
再來到高雄市的橋頭區,擔任幼稚園園長的尤蒍葭,家裡三米深、三面無牆的大陽台是她的最愛。「我常請園內的老師來家裡的聚餐,因為可以或坐或站,視野又無比開闊,比起在室內的用餐,大家都更喜歡來陽台。」
事實上,為了讓陽台更賞心悅目,與朋友歡聚的時光更美好,尤蒍葭還巧妙運用南台灣豐沛的光照,選購芒草狀與環繞型的迷你太陽能燈泡,安裝在陽台的四周。
「通常在吸飽了一整天的熱能後,從傍晚五、六點起,它們就會開始發亮,持續『盛開』到十點左右,這當中的時間,也是陽台最繽紛的魔幻時刻。」
尤蒍葭說,美感對她來說,是生活品質的基礎,而陽台以其半自然、半戶外得天獨厚的條件,又比一室之內的其他空間,擁有更多的彈性與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