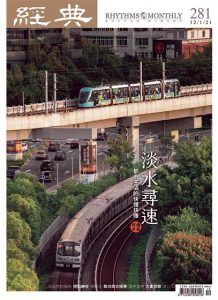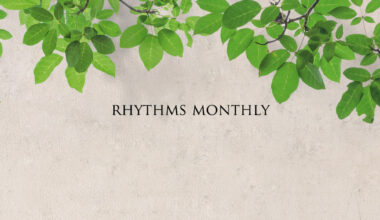前幾天我突然注意到今年對我來說,是個非常不尋常的年。
我在一九九八年與內人結束了在美國「23」年行醫教學的歲月,想不到回國服務,轉眼間又過了另一個「23」年。
第一個「23」年(1975-1998)
記得一九七五年我在台大醫院神經精神科完成四年住院醫師訓練,又做了一年主治醫師,內人也完成了住院醫師訓練,我們雙雙到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醫院受訓。由於美國並不承認國外的畢業後訓練,所以我又從第一年神經內科住院醫師開始做起,完成整整三年的住院醫師訓練,接著我又接受一年的癲癇與腦波專研醫師訓練,而後轉到堪薩斯大學醫院,展開我的教學、服務與研究生涯。十九年後,我終於回到故鄉。
坦白說,在國內求學就職一直相當順利,很少受到挫折,但初到美國時,因為是有生以來首次出國,生活習慣很難適應,同時發現自以為沒問題的英文竟是一大問題。我聽不懂許多美國人的slang(俚語)或幽默,而對方也聽不太懂我帶有口音的英文,自然而然,別人無從「公平地」評估我的能力。因為語言文化的隔閡而嘗到的酸甜苦辣是在國內從未遭遇到的經驗,也才有機會嘗到被誤解、歧視的滋味。
由於對腦波的興趣,很自然地我的興趣也轉向腦波最有臨床診斷價值的癲癇。透過長期照顧因為癲癇而遭受誤解與偏見的病人,才了解罹患被汙名化的疾病者的內心世界。
不知不覺因為自己早期在美國所遭受的溝通困難,以及照顧癲癇病人的心得,使我能對弱勢族群「將心比心」,而這「同理心」(empathy)的培養使我對病人的感受更具有「敏感度」,更了解在醫病籓籬另一邊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