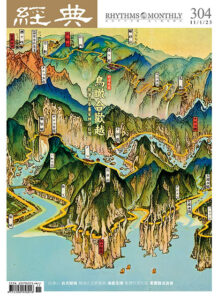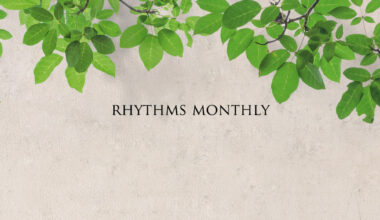記得剛回國時,父親已經九十一歲,當時我與內人都在花蓮慈濟大學醫學院服務。週末回台北看他時,我們最高興的,就是陪他老人家參加他與「老朋友」在當時國賓飯店二樓的週日粵式飲茶聚餐。
大家都在上午九點準時出席,屬羊的父親是他們這些老人的領頭「羊」,他以下都是八十幾歲的,以及一位「最年輕的七十八歲歐吉桑。他們之中只有一對比父親小幾歲的夫妻結伴出席,其他都是像父親一樣,另一半已仙去的鰥夫,話匣子一打開就是你一句我一句的接下去。
我們最初常想笑的是他們因為聽力不好,彼此常常答非所問,但我和太太這兩個「年輕人」看到他們談笑風生好不高興的樣子,才發現,上了年紀的人與老友暢談,重要的並不在於「雙方對談」,而是有老友當「抒發己見」的聽眾,我們也不知不覺融入他們的歡笑中。等到用完餐,我給他們牙籤時,每個人都搖頭,「我們不需要。」這才注意到,他們的確沒有多少牙齒。十一點一到,大家都準時結束,歡笑而別。
在回家的路上,我注意到父親因為這一場餐敘而心情開朗許多,並會主動與我談一些心裡的話。很明顯地,父親自從母親過世以來,只有在這老人的餐敘,才重現開朗健談的風光。這讓我學到,「老人應該用心找尋能使自己快樂的方法」。
而今,父親已經在我回國十年後,以一百零一歲高齡離開人間,我也已回國二十五年,再幾個月後即將由七十幾歲的「耊」(發音如「蝶」)堂堂進入八十幾歲的「耄」(發音如「帽」)。最近幾位中學、大學的同學不告而別,更使我回想起老父當年與老友歡聚的許多場景,而越能體會老人的「相見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