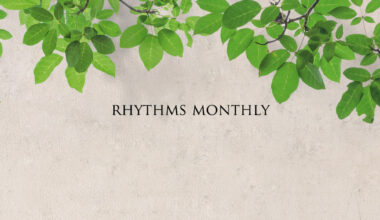最近參加一個醫學教育基金會的董事會,主席提出一個非常有創意的培育醫學院畢業後醫學教育計畫,希望能給一些優秀的台灣年輕醫師,除了國內要求的臨床經驗的訓練外,並提供海內外進修課程,建立群體關係,並有一年半時間赴美國名校進行海外碩士學位培訓,以培養台灣最優秀的年輕醫師。由於所費不貲,引起一些討論。有位董事提問,如果這些學員在國外訓練結束後,改變初衷決定不回來履約的話,我們有沒有賠款或懲罰的辦法,因而引起諸多討論。最後主席的一句話讓我非常感動:「我們注意選才,希望找到有理想有心要為台灣做事的年輕人,但萬一他改變看法,不想回國服務的話,我們也算是盡了培育人才的目標,雖然他這年紀可能改變了想法,但如果後來他還是回到台灣,說不定對台灣的幫忙會更大。」最後全場通過了這提案,但這討論卻觸動了我一直深藏內心之痛。
我很少主動提起這事隔四十多年的陳年往事,因為這是我到今天仍無法釋懷的曾經「失信於人」的憾事。我在一九六九年由台大醫學院畢業,服完兵役之後,進入台大醫院完成四年神經精神科(當年這兩科仍未分家)住院醫師訓練,並當了一年主治醫師,於一九七五年在台大醫院「留職停薪」安排下,到美國進修兩年。想不到我到了明尼蘇達大學醫院之後,才知道大學醫院的安排,是我需要完成為期三年的完整住院醫師訓練。神經科主任Dr. A. B. Baker是美國神經醫學會創會會長,他告訴我,他訓練過許多國外的神經學學者,不管多資深,他都有把握,經過他用心設計的循序漸進的制度下,學到扎實的臨床神經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