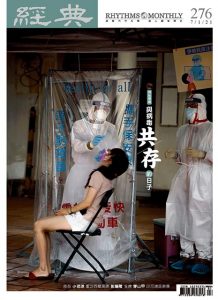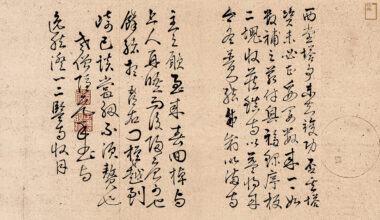肆虐全球將達兩年的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 pandemic)是二十一世紀初始最大的公衛災難,疫苗成了人類對抗這場災疫的盾牌。在短時間即開發成功,完成臨床試驗,開始大規模施打的信使核糖核酸(messenger ribonucleic acid,mRNA)疫苗立了大功,成為不幸中的大幸。過往所有的疫苗開發皆耗年費時,此次人類史上第一款mRNA疫苗卻不到一年即上市,這不是mRNA疫苗製作與發明過程容易,而是背後累積了凱特琳.卡瑞柯(Katalin Karikó)及其合作者多年來堅持基礎研究的心酸血淚。
mRNA是不穩定的單股核糖核酸,它帶有來自DNA(去氧核糖核酸)的遺傳信息,可轉譯成蛋白質。一九八○年代分子生物學理論及方法雖日新月異,但對於mRNA的基礎研究,包括如何在實驗室中合成mRNA,以及如何將mRNA送入細胞,再利用其所攜帶的遺傳信息製造蛋白質還是非常困難。而扭轉mRNA研究發展趨勢的,正是現年六十六歲的凱特琳.卡瑞柯博士。
凱特琳生長於匈牙利,雖然成長環境中從未接觸過科學家,卻從小就立志從事科研。凱特琳在賽格德大學(University of Szeged)攻得博士學位後,留在大學內的生物學研究中心從事博士後研究。一九八五年,凱特琳所工作的生物學研究中心經費告磬,她在匈牙利也找不到研究職位,於是她與丈夫帶著兩歲的女兒飄洋過海前往美國費城的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擔任博士後研究員。當時匈牙利政府管制外滙,出國換滙的上限是一百歐元。為了多帶點錢出國,以確保一家人初抵異國時生活無虞,她只能和丈夫將九百歐元縫入女兒蘇珊的泰迪熊中,夾帶出國。
雖然當時RNA的基礎研究仍然相當困難。不過,凱特琳卻對mRNA情有獨鍾,她全心投入相關實驗。由於mRNA具有不穩定、難以保存的特質,連細胞裡內生的mRNA都很容易產生被分解成更簡單小分子的降解現象(degradation)了,更何況打算從細胞外送進mRNA,使其在細胞內製造蛋白質。因這個主意看似太過理想化,不切實際,所以凱特琳申請研究經費屢屢挫敗。她不但遭到多數科學家同儕的嘲笑,更因為爭取經費不利,長期只能屈居最低階的助理研究員,無法獲得正式教職。即使如此,凱特琳仍堅持著對mRNA的熱愛,維持著最低的生活條件,持續地找尋不但能將mRNA送進細胞表達蛋白質,且可「逃過」被免疫系統破壞的解方。